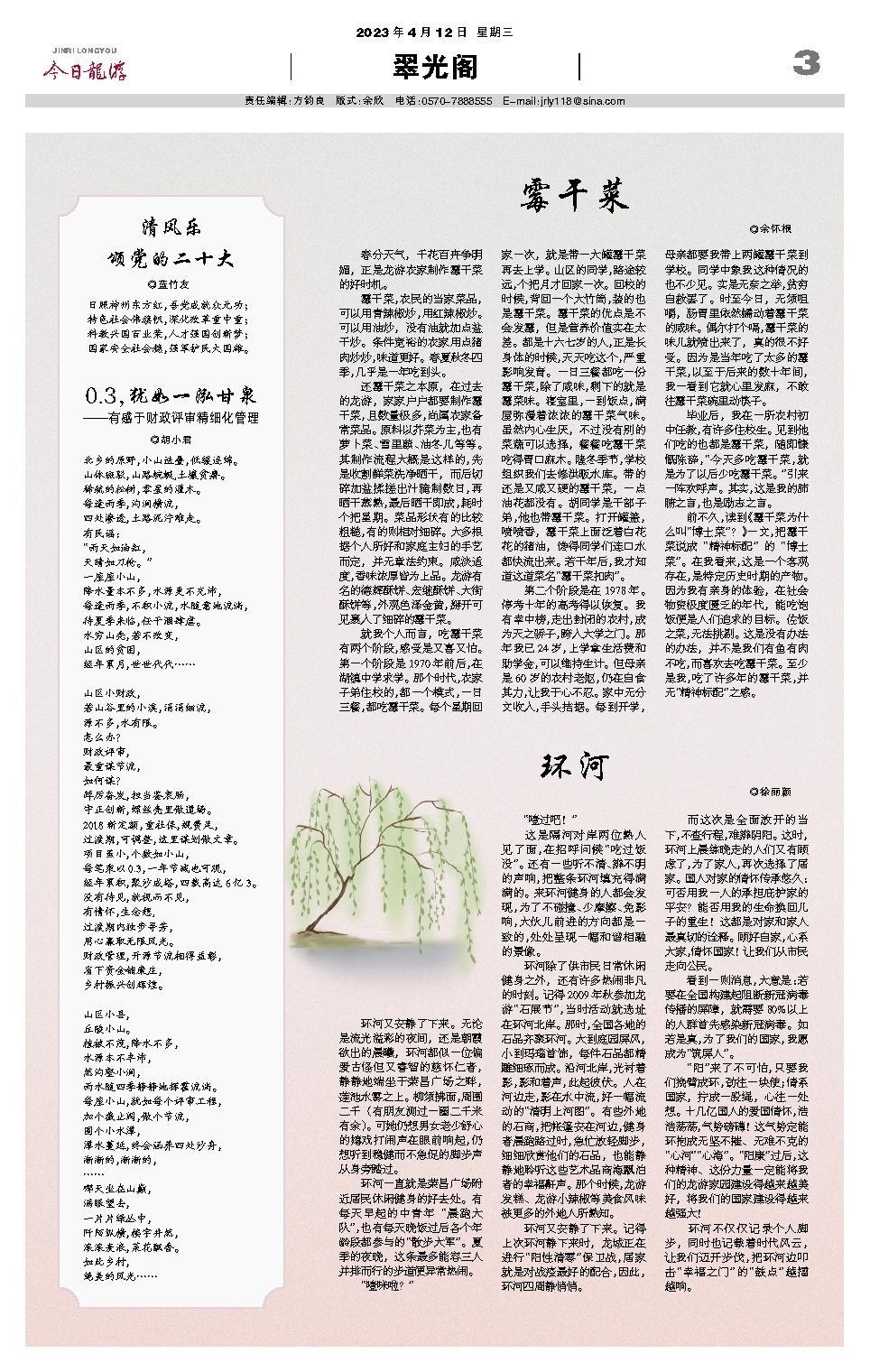◎余怀根
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正是龙游农家制作霉干菜的好时机。
霉干菜,农民的当家菜品,可以用青辣椒炒,用红辣椒炒。可以用油炒,没有油就加点盐干炒。条件宽裕的农家用点猪肉炒炒,味道更好。春夏秋冬四季,几乎是一年吃到头。
还霉干菜之本原,在过去的龙游,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霉干菜,且数量极多,尚属农家备常菜品。原料以芥菜为主,也有萝卜菜、雪里蕻、油冬儿等等。其制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收割鲜菜洗净晒干,而后切碎加盐揉搓出汁腌制数日,再晒干蒸熟,最后晒干即成,耗时个把星期。菜品形状有的比较粗糙,有的则相对细碎。大多根据个人所好和家庭主妇的手艺而定,并无章法约束。咸淡适度,香味浓厚皆为上品。龙游有名的德辉酥饼、宏继酥饼、大街酥饼等,外观色泽金黄,掰开可见裹入了细碎的霉干菜。
就我个人而言,吃霉干菜有两个阶段,感受是又喜又怕。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前后,在湖镇中学求学。那个时代,农家子弟住校的,都一个模式,一日三餐,都吃霉干菜。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就是带一大罐霉干菜再去上学。山区的同学,路途较远,个把月才回家一次。回校的时候,背回一个大竹筒,装的也是霉干菜。霉干菜的优点是不会发霉,但是营养价值实在太差。都是十六七岁的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吃这个,严重影响发育。一日三餐都吃一份霉干菜,除了咸味,剩下的就是霉菜味。寝室里,一到饭点,满屋弥漫着浓浓的霉干菜气味。虽然内心生厌,不过没有别的菜蔬可以选择,餐餐吃霉干菜吃得胃口麻木。隆冬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去修洪畈水库。带的还是又咸又硬的霉干菜,一点油花都没有。胡同学是干部子弟,他也带霉干菜。打开罐盖,喷喷香,霉干菜上面泛着白花花的猪油,馋得同学们连口水都快流出来。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道菜名“霉干菜扣肉”。
第二个阶段是在1978年。停考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我有幸中榜,走出封闭的农村,成为天之骄子,跨入大学之门。那年我已24岁,上学拿生活费和助学金,可以维持生计。但母亲是60岁的农村老妪,仍在自食其力,让我于心不忍。家中无分文收入,手头拮据。每到开学,母亲都要我带上两罐霉干菜到学校。同学中象我这种情况的也不少见。实是无奈之举,贫穷自救罢了。时至今日,无须咀嚼,肠胃里依然蠕动着霉干菜的咸味。偶尔打个嗝,霉干菜的味儿就喷出来了,真的很不好受。因为是当年吃了太多的霉干菜,以至于后来的数十年间,我一看到它就心里发麻,不敢往霉干菜碗里动筷子。
毕业后,我在一所农村初中任教,有许多住校生。见到他们吃的也都是霉干菜,随即慷慨陈辞,“今天多吃霉干菜,就是为了以后少吃霉干菜。”引来一阵欢呼声。其实,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励志之言。
前不久,读到《霉干菜为什么叫“博士菜”?》一文,把霉干菜说成“精神标配”的“博士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为我有亲身的体验,在社会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吃饱饭便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佐饭之菜,无法挑剔。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不是我们有鱼有肉不吃,而喜欢去吃霉干菜。至少是我,吃了许多年的霉干菜,并无“精神标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