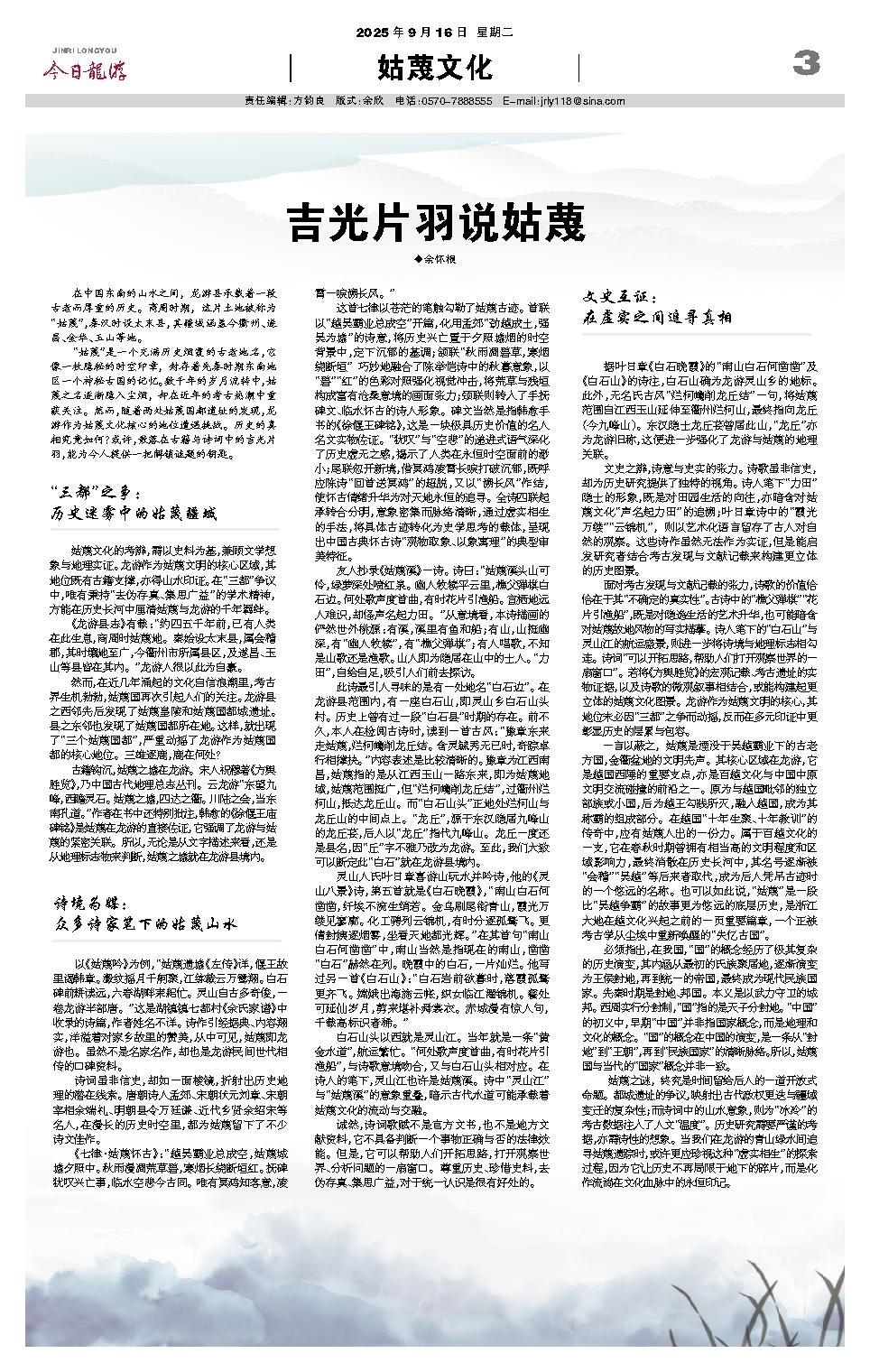◆余怀根
在中国东南的山水之间,龙游县承载着一段古老而厚重的历史。商周时期,这片土地被称为“姑蔑”,秦汉时设太末县,其疆域涵盖今衢州、遂昌、金华、玉山等地。
“姑蔑”是一个充满历史烟霞的古老地名,它像一枚隐秘的时空印章,封存着先秦时期东南地区一个神秘古国的记忆。数千年的岁月流转中,姑蔑之名逐渐隐入尘烟,却在近年的考古热潮中重获关注。然而,随着两处姑蔑国都遗址的发现,龙游作为姑蔑文化核心的地位遭遇挑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许,散落在古籍与诗词中的吉光片羽,能为今人提供一把解锁谜题的钥匙。
“三都”之争: 历史迷雾中的姑蔑疆域
姑蔑文化的考辨,需以史料为基,兼顾文学想象与地理实证。龙游作为姑蔑文明的核心区域,其地位既有古籍支撑,亦得山水印证。在“三都”争议中,唯有秉持“去伪存真、集思广益”的学术精神,方能在历史长河中厘清姑蔑与龙游的千年羁绊。
《龙游县志》有载:“约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息,商周时姑蔑地。秦始设太末县,属会稽郡,其时壤地至广,今衢州市所属县区,及遂昌、玉山等县皆在其内。”龙游人很以此为自豪。
然而,在近几年涌起的文化自信浪潮里,考古界生机勃勃,姑蔑国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龙游县之西邻先后发现了姑蔑皇陵和姑蔑国都城遗址。县之东邻也发现了姑蔑国都所在地。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姑蔑国都”,严重动摇了龙游作为姑蔑国都的核心地位。三雄逐鹿,鹿在何处?
古籍钩沉,姑蔑之墟在龙游。宋人祝穆著《方舆胜览》,乃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云龙游“东望九峰,西瞻灵石。姑蔑之墟,四达之衢。川陆之会,当东南孔道。”作者在书中还特别批注,韩愈的《徐偃王庙碑铭》是姑蔑在龙游的直接佐证,它强调了龙游与姑蔑的紧密关联。所以,无论是从文字描述来看,还是从地理标志物来判断,姑蔑之墟就在龙游县境内。
诗境为媒: 众多诗家笔下的姑蔑山水
以《姑蔑吟》为例,“姑蔑遗墟《左传》详,偃王故里谒韩章。瀫纹摇月千舸聚,江练裁云万鹭翔。白石碑前耕读远,六春湖畔耒耜忙。灵山自古多奇俊,一卷龙游半部唐。”这是湖镇镇七都村《余氏家谱》中收录的诗篇,作者姓名不详。诗作引经据典、内容翔实,洋溢着对家乡故里的赞美,从中可见,姑蔑即龙游也。虽然不是名家名作,却也是龙游民间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
诗词虽非信史,却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历史地理的潜在线索。唐朝诗人孟郊、宋朝状元刘章、宋朝宰相余端礼、明朝县令万廷谦、近代乡贤余绍宋等名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都为姑蔑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
《七律·姑蔑怀古》:“越吴霸业总成空,姑蔑城墟夕照中。秋雨漫凋荒草碧,寒烟长绕断垣红。抚碑犹叹兴亡事,临水空悲今古同。唯有冥鸿知客意,凌霄一唳溯长风。”
这首七律以苍茫的笔触勾勒了姑蔑古迹。首联以“越吴霸业总成空”开篇,化用孟郊“劲越成土,强吴为墟”的诗意,将历史兴亡置于夕照墟烟的时空背景中,定下沉郁的基调;颔联“秋雨凋碧草,寒烟绕断垣”巧妙地融合了陈举恺诗中的秋暮意象,以“碧”“红”的色彩对照强化视觉冲击,将荒草与残垣构成富有沧桑意境的画面张力;颈联则转入了手抚碑文、临水怀古的诗人形象。碑文当然是指韩愈手书的《徐偃王碑铭》,这是一块极具历史价值的名人名文实物佐证。“犹叹”与“空悲”的递进式语气深化了历史虚无之感,揭示了人类在永恒时空面前的渺小;尾联忽开新境,借冥鸿凌霄长唳打破沉郁,既呼应陈诗“回首送冥鸿”的超脱,又以“溯长风”作结,使怀古情绪升华为对天地永恒的追寻。全诗四联起承转合分明,意象密集而脉络清晰,通过虚实相生的手法,将具体古迹转化为史学思考的载体,呈现出中国古典怀古诗“观物取象、以象寓理”的典型审美特征。
友人抄录《姑蔑溪》一诗。诗曰:“姑蔑溪头山可怜,绿萝深处喷红泉。幽人牧犊平云里,樵父弾棋白石边。何处歌声度首曲,有时花片引渔船。宜栖地远人难识,却怪声名起力田。”从意境看,本诗描画的俨然世外桃源:有溪,溪里有鱼和船;有山,山挺幽深,有“幽人牧犊”,有“樵父弾棋”;有人唱歌,不知是山歌还是渔歌。山人即为隐居在山中的士人。“力田”,自给自足,吸引人们前去探访。
此诗最引人寻味的是有一处地名“白石边”。在龙游县范围内,有一座白石山,即灵山乡白石山头村。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白石县”时期的存在。前不久,本人在检阅古诗时,读到一首古风:“豫章东来走姑蔑,烂柯巉削龙丘结。含灵毓秀无已时,奇踪卓行相撑抉。”内容表述是比较清晰的。豫章为江西南昌,姑蔑指的是从江西玉山一路东来,即为姑蔑地域,姑蔑范围挺广,但“烂柯巉削龙丘结”,过衢州烂柯山,抵达龙丘山。而“白石山头”正地处烂柯山与龙丘山的中间点上。“龙丘”,源于东汉隐居九峰山的龙丘苌,后人以“龙丘”指代九峰山。龙丘一度还是县名,因“丘”字不雅乃改为龙游。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此“白石”就在龙游县境内。
灵山人氏叶日章喜游山玩水并吟诗,他的《灵山八景》诗,第五首就是《白石晚霞》,“南山白石何凿凿,纤埃不涴生绡若。金乌刷尾衔青山,霞光万缕见寥廓。化工骋列云锦机,有时分逐孤鹜飞。更倩封姨逐烟雾,坐看天地都光辉。”在其首句“南山白石何凿凿”中,南山当然是指现在的南山,凿凿“白石”赫然在列。晚霞中的白石,一片灿烂。他写过另一首《白石山》:“白石岩前欲暮时,落霞孤鹜更齐飞。嫦娥出海施云帐,织女临江濯锦机。餐处可延仙岁月,剪来堪补舜裳衣。赤城漫有惊人句,千载高标识者稀。”
白石山头以西就是灵山江。当年就是一条“黄金水道”,航运繁忙。“何处歌声度首曲,有时花片引渔船”,与诗歌意境吻合,又与白石山头相对应。在诗人的笔下,灵山江也许是姑蔑溪。诗中“灵山江”与“姑蔑溪”的意象重叠,暗示古代水道可能承载着姑蔑文化的流动与交融。
诚然,诗词歌赋不是官方文书,也不是地方文献资料,它不具备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的法律效能。但是,它可以帮助人们开拓思路,打开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一扇窗口。尊重历史、珍惜史料,去伪存真、集思广益,对于统一认识是很有好处的。
文史互证: 在虚实之间追寻真相
据叶日章《白石晚霞》的“南山白石何凿凿”及《白石山》的诗注,白石山确为龙游灵山乡的地标。此外,无名氏古风“烂柯巉削龙丘结”一句,将姑蔑范围自江西玉山延伸至衢州烂柯山,最终指向龙丘(今九峰山)。东汉隐士龙丘苌曾居此山,“龙丘”亦为龙游旧称,这便进一步强化了龙游与姑蔑的地理关联。
文史之辨,诗意与史实的张力。诗歌虽非信史,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诗人笔下“力田”隐士的形象,既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亦暗含对姑蔑文化“声名起力田”的追溯;叶日章诗中的“霞光万缕”“云锦机”,则以艺术化语言留存了古人对自然的观察。这些诗作虽然无法作为实证,但是能启发研究者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构建更立体的历史图景。
面对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张力,诗歌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不确定的真实性”。古诗中的“樵父弾棋”“花片引渔船”,既是对隐逸生活的艺术升华,也可能暗含对姑蔑故地风物的写实描摹。诗人笔下的“白石山”与灵山江的航运盛景,则进一步将诗境与地理标志相勾连。诗词“可以开拓思路,帮助人们打开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若将《方舆胜览》的宏观记载、考古遗址的实物证据,以及诗歌的微观叙事相结合,或能构建起更立体的姑蔑文化图景。龙游作为姑蔑文明的核心,其地位未必因“三都”之争而动摇,反而在多元印证中更彰显历史的层累与包容。
一言以蔽之,姑蔑是湮没于吴越霸业下的古老方国,金衢盆地的文明先声。其核心区域在龙游,它是越国西陲的重要支点,亦是百越文化与中国中原文明交流碰撞的前沿之一。原为与越国毗邻的独立部族或小国,后为越王勾践所灭,融入越国,成为其称霸的组成部分。在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传奇中,应有姑蔑人出的一份力。属于百越文化的一支,它在春秋时期曾拥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和区域影响力,最终消散在历史长河中,其名号逐渐被“会稽”“吴越”等后来者取代,成为后人凭吊古迹时的一个悠远的名称。也可以如此说,“姑蔑”是一段比“吴越争霸”的故事更为悠远的底层历史,是浙江大地在越文化兴起之前的一页重要篇章,一个正被考古学从尘埃中重新唤醒的“失忆古国”。
必须指出,在我国,“国”的概念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其内涵从最初的氏族聚居地,逐渐演变为王侯封地,再到统一的帝国,最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先秦时期是封地、邦国。本义是以武力守卫的城邦。西周实行分封制,“国”指的是天子分封地。“中国”的初义中,早期“中国”并非指国家概念,而是地理和文化的概念。“国”的概念在中国的演变,是一条从“封地”到“王朝”,再到“民族国家”的清晰脉络。所以,姑蔑国与当代的“国家”概念并非一致。
姑蔑之谜,终究是时间留给后人的一道开放式命题。都城遗址的争议,映射出古代政权更迭与疆域变迁的复杂性;而诗词中的山水意象,则为“冰冷”的考古数据注入了人文“温度”。历史研究需要严谨的考据,亦需诗性的想象。当我们在龙游的青山绿水间追寻姑蔑遗踪时,或许更应珍视这种“虚实相生”的探索过程,因为它让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下的碎片,而是化作流淌在文化血脉中的永恒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