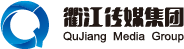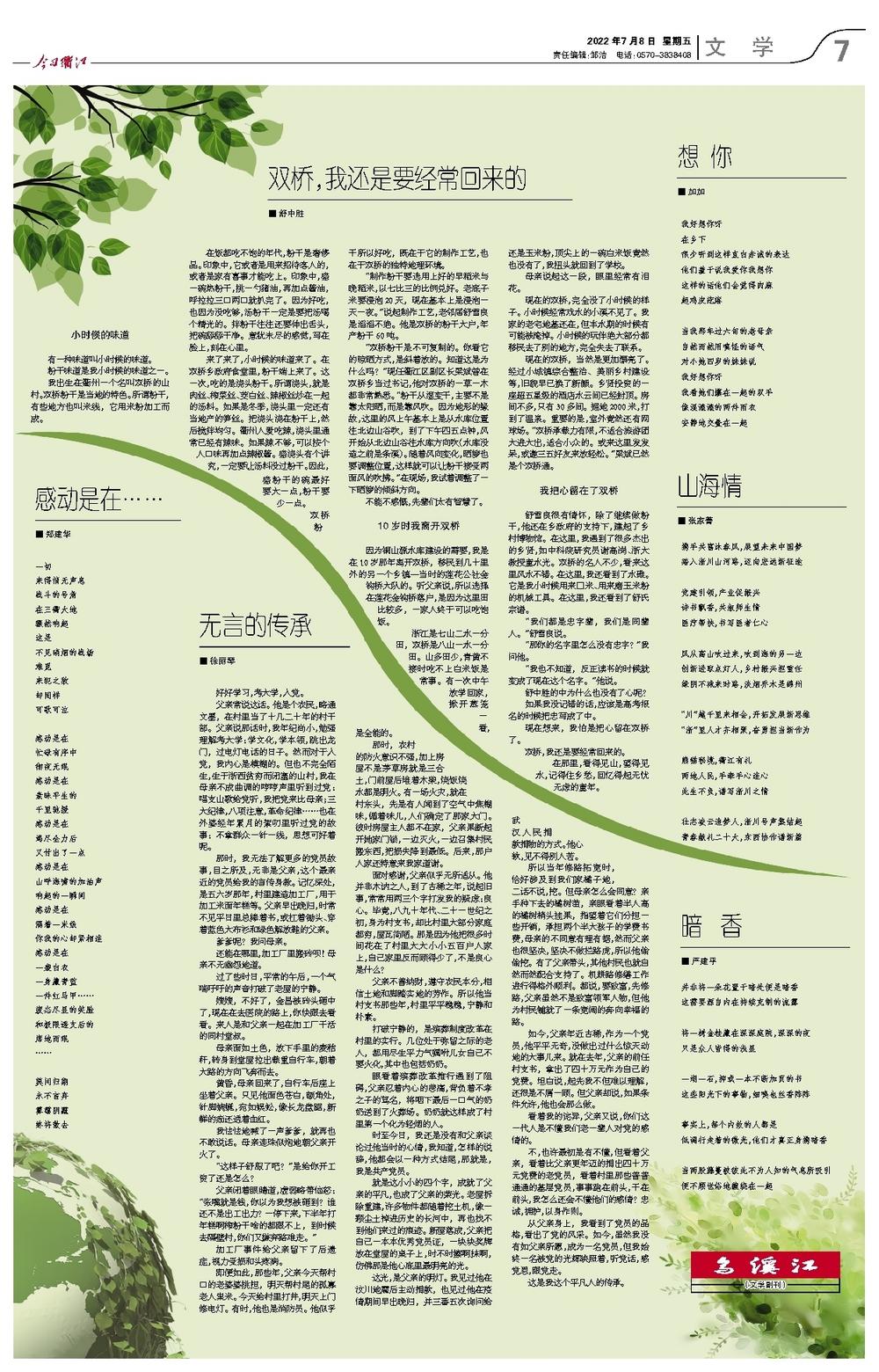■ 徐丽琴
好好学习,考大学,入党。
父亲常说这话。他是个农民,略通文墨,在村里当了十几二十年的村干部。父亲说那话时,我年纪尚小,勉强理解考大学:学文化,学本领,跳出龙门,过电灯电话的日子。然而对于入党,我内心是模糊的。但也不完全陌生,生于浙西贫穷而闭塞的山村,我在母亲不成曲调的哼哼声里听到过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纪律……也在外婆经年累月的絮叨里听过党的故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思想可好着呢。
那时,我无法了解更多的党员故事,目之所及,无非是父亲,这个最亲近的党员给我的言传身教。记忆深处,是五六岁那年,村里建造加工厂,用于加工米面年糕等。父亲早出晚归,时常不见平日里总捧着书,或扛着锄头、穿着蓝色大布衫和绿色解放鞋的父亲。
爹爹呢?我问母亲。
还能在哪里,加工厂里搬砖呗!母亲不无幽怨地道。
过了些时日,平常的午后,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打破了老屋的宁静。
嫂嫂,不好了,金昌被砖头砸中了,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你快跟去看看。来人是和父亲一起在加工厂干活的同村堂叔。
母亲面如土色,放下手里的麦秸秆,转身到堂屋拉出载重自行车,朝着大路的方向飞奔而去。
黄昏,母亲回来了,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父亲。只见他面色苍白,额角处,针脚蜿蜒,宛如蜈蚣,像长龙盘踞,新鲜的痂还透着血红。
我怯怯地喊了一声爹爹,就再也不敢说话。母亲连珠似炮地朝父亲开火了。
“这样子舒服了吧?”是给你开工资了还是怎么?
父亲闭着眼睛道,虚弱略带恼怒:“张嘴就是钱,你以为我想被砸到?谁还不是出工出力?一停下来,下半年打年糕啊榨粉干啥的都跟不上,到时候去隔壁村,你们又嫌弃路难走。”
加工厂事件给父亲留下了后遗症,视力受损和头疼病。
即便如此,那些年,父亲今天帮村口的老婆婆挑担,明天帮村尾的孤寡老人粜米。今天给村里打井,明天上门修电灯。有时,他也是消防员。他似乎是全能的。
那时,农村的防火意识不强,加上房屋不是茅草房就是三合土,门前屋后堆着木柴,烧饭烧水都是明火。有一场火灾,就在村东头,先是有人闻到了空气中焦糊味,循着味儿,人们确定了那家大门。彼时房屋主人都不在家,父亲果断起开她家门锁,一边灭火,一边召集村民搬东西,把损失降到最低。后来,那户人家还特意来我家道谢。
面对感谢,父亲似乎无所适从。他并非木讷之人,到了古稀之年,说起旧事,常常用两三个字打发我的疑虑:良心。毕竟,八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之初,身为村支书,却比村里大部分家庭都穷,屋瓦简陋。那是因为他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村里大大小小五百户人家上,自己家里反而顾得少了,不是良心是什么?
父亲不善纳财,遵守农民本分,相信土地和脚踏实地的劳作。所以他当村支书那些年,村里平平稳稳,宁静和朴素。
打破宁静的,是殡葬制度改革在村里的实行。几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都用尽生平力气嘱咐儿女自己不要火化,其中也包括奶奶。
眼看着殡葬改革推行遇到了阻碍,父亲忍着内心的悲痛,背负着不孝之子的骂名,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奶奶送到了火葬场。奶奶就这样成了村里第一个化为轻烟的人。
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和父亲谈论过他当时的心情,我知道,怎样的说辞,他都会以一种方式结尾,那就是,我是共产党员。
就是这小小的四个字,成就了父亲的平凡,也成了父亲的荣光。老屋拆除重建,许多物件都随着挖土机,像一颗尘土掉进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找不到他们来过的痕迹。新屋落成,父亲把自己一本本优秀党员证,一块块奖牌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时不时擦啊抹啊,仿佛那是他心底里最明亮的光。
这光,是父亲的明灯。我见过他在汶川地震后主动捐款,也见过他在疫情期间早出晚归,并三番五次询问给武汉人民捐款捐物的方式。他心软,见不得别人苦。
所以当年修路拓宽时,恰好涉及到我们家橘子地,二话不说,挖。但母亲怎么会同意?亲手种下去的橘树苗,亲眼看着半人高的橘树梢头挂果,指望着它们分担一些开销,承担两个半大孩子的学费书费,母亲的不同意有理有据,然而父亲也很坚决,坚决不做拦路虎,所以他偷偷挖。有了父亲带头,其他村民也就自然而然配合支持了。机耕路修缮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都说,要致富,先修路,父亲虽然不是致富领军人物,但他为村民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奔向幸福的路。
如今,父亲年近古稀,作为一个党员,他平平无奇,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在去年,父亲的前任村支书,拿出了四十万元作为自己的党费。坦白说,起先我不但难以理解,还很是不屑一顾。但父亲却说,如果条件允许,他也会那么做。
看着我的诧异,父亲又说,你们这一代人是不懂我们老一辈人对党的感情的。
不,也许最初是有不懂,但看着父亲,看着比父亲更年迈的捐出四十万元党费的老党员,看着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事事跑在前头,干在前头,我怎么还会不懂他们的感情?忠诚,拥护,以身作则。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党员的品格,看出了党的风采。如今,虽然我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党员,但我始终一名被党的光辉映照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是我这个平凡人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