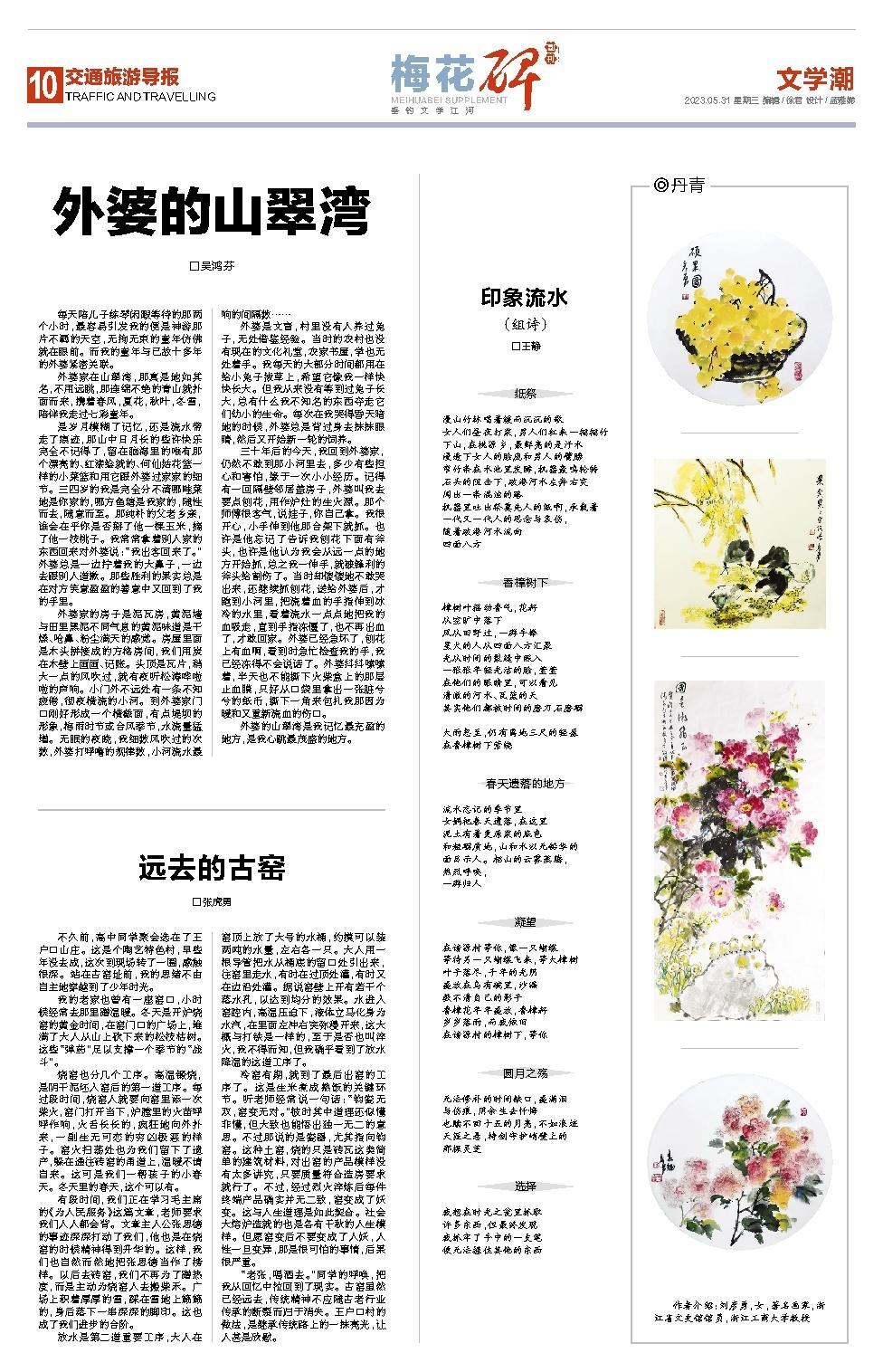不久前,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了王户口山庄。这是个陶艺特色村,早些年没去成,这次到现场转了一圈,感触很深。站在古窑址前,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穿越到了少年时光。
我的老家也曾有一座窑口,小时候经常去那里蹭温暖。冬天是开炉烧窑的黄金时间,在窑门口的广场上,堆满了大人从山上砍下来的松枝枯树。这些“弹药”足以支撑一个季节的“战斗”。
烧窑也分几个工序。高温锻烧,是阴干泥坯入窑后的第一道工序。每过段时间,烧窑人就要向窑里添一次柴火,窑门打开当下,炉膛里的火苗呼呼作响,火舌长长的,疯狂地向外扑来,一副生无可恋的穷凶极恶的样子。窑火扫荡处也为我们留下了遗产,躲在通往砖窑的甬道上,温暖不请自来。这可是我们一帮孩子的小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这个可以有。
有段时间,我们正在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老师要求我们人人都会背。文章主人公张思德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们,他也是在烧窑的时候精神得到升华的。这样,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张思德当作了榜样。以后去砖窑,我们不再为了蹭热度,而是主动为烧窑人去搬柴禾。广场上积着厚厚的雪,踩在雪地上籁籁的,身后落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也成了我们进步的台阶。
放水是第二道重要工序,大人在窑顶上放了大号的水桶,约摸可以装两吨的水量,左右各一只。大人用一根导管把水从桶底的留口处引出来,往窑里走水,有时在过顶处灌,有时又在边沿处灌。据说窑壁上开有若干个落水孔,以达到均分的效果。水进入窑腔内,高温压迫下,液体立马化身为水汽,在里面左冲右突弥漫开来,这大概与打铁是一样的,至于是否也叫淬火,我不得而知,但我确乎看到了放水降温的这道工序了。
冷窑有期,就到了最后出窑的工序了。这是生米煮成熟饭的关键环节。听老师经常说一句话:“钧瓷无双,窑变无对。”彼时其中道理还似懂非懂,但大致也能悟出独一无二的意思。不过那说的是瓷器,尤其指向钧窑。这种土窑,烧的只是砖瓦这类简单的建筑材料,对出窑的产品模样没有太多讲究,只要质量符合造房要求就行了。不过,经过烈火淬炼后每件终端产品确实并无二致,窑变成了妖变。这与人生道理是如此契合。社会大熔炉造就的也是各有千秋的人生模样。但愿窑变后不要变成了人妖,人性一旦变异,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后果很严重。
“老张,喝酒去。”同学的呼唤,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古窑虽然已经远去,传统精神不应随古老行业传承的断裂而归于消失。王户口村的做法,是继承传统路上的一抹亮光,让人甚是欣慰。
□张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