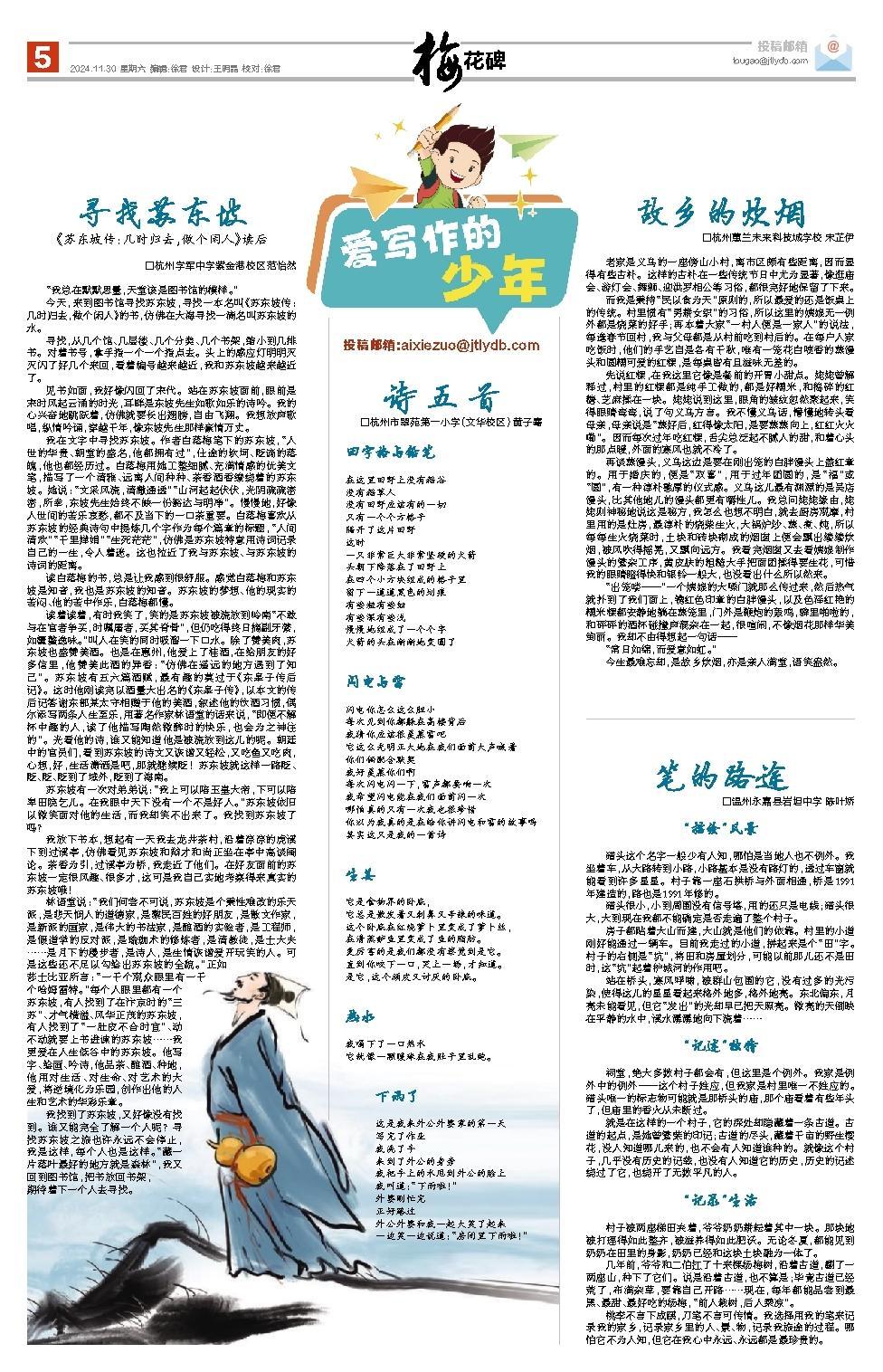“描绘”风景
碏头这个名字一般少有人知,哪怕是当地人也不例外。我坐着车,从大路转到小路,小路基本是没有路灯的,透过车窗就能看到许多星星。村子靠一座石拱桥与外面相通,桥是1991年建造的,路也是1991年修的。
碏头很小,小到周围没有信号塔,用的还只是电线;碏头很大,大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是否走遍了整个村子。
房子都贴着大山而建,大山就是他们的依靠。村里的小道刚好能通过一辆车。目前我走过的小道,拼起来是个“田”字。村子的右侧是“坑”,将田和房屋划分,可能以前那儿还不是田时,这“坑”起着护城河的作用吧。
站在桥头,寒风呼啸,被群山包围的它,没有过多的光污染,使得这儿的星星看起来格外地多,格外地亮。东北偏东,月亮未能看见,但它“发出”的光却早已把天照亮。微亮的天倒映在平静的水中,溪水潺潺地向下流着……
“记述”独特
祠堂,绝大多数村子都会有,但这里是个例外。我家是例外中的例外——这个村子姓应,但我家是村里唯一不姓应的。碏头唯一的标志物可能就是那桥头的庙,那个庙看着有些年头了,但庙里的香火从未断过。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子,它的深处却隐藏着一条古道。古道的起点,是她曾繁荣的印记;古道的尽头,藏着千亩的野生樱花,没人知道哪儿来的,也不会有人知道谁种的。就像这个村子,几乎没有历史的记载,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历史的记述绕过了它,也绕开了无数平凡的人。
“记录”生活
村子被两座梯田夹着,爷爷奶奶耕耘着其中一块。那块地被打理得如此整齐,被滋养得如此肥沃。无论冬夏,都能见到奶奶在田里的身影,奶奶已经和这块土块融为一体了。
几年前,爷爷和二伯扛了十来棵杨梅树,沿着古道,翻了一两座山,种下了它们。说是沿着古道,也不算是;毕竟古道已经荒了,布满杂草,要靠自己开路……现在,每年都能品尝到最黑、最甜、最好吃的杨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桃李不言下成蹊,刀笔不言可传情。我选择用我的笔来记录我的家乡,记录家乡里的人、景、物,记录我旅途的过程。哪怕它不为人知,但它在我心中永远、永远都是最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