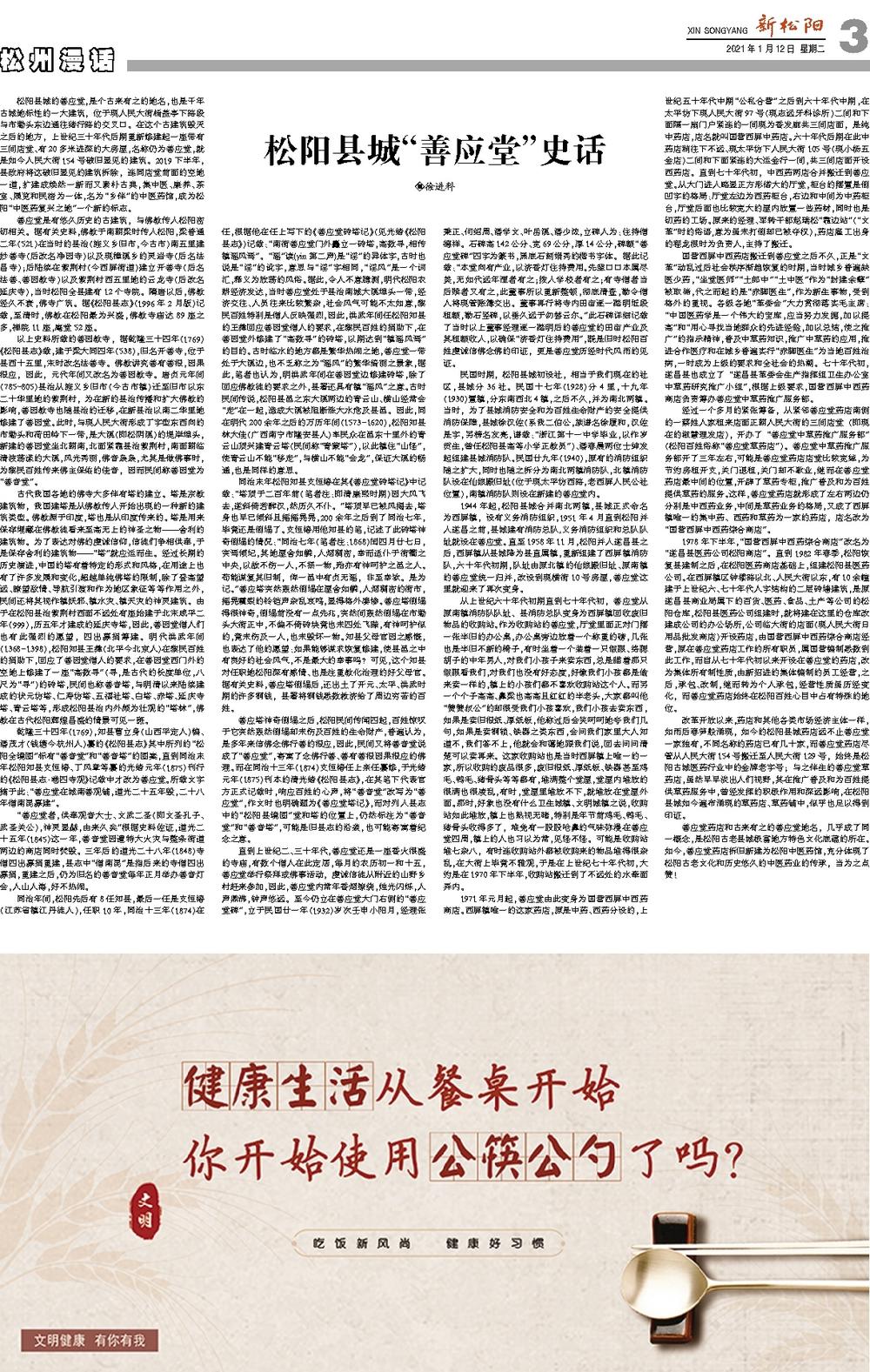松阳县城的善应堂,是个古来有之的地名,也是千年古城地标性的一大建筑,位于现人民大街桶盖亭下路段与市◇头东边通往猪行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古建筑毁灭之后的地方,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重新修建起一座带有三间店堂、有20多米进深的大房屋,名称仍为善应堂,就是如今人民大街154号破旧显见的建筑。2019下半年,县政府将这破旧显见的建筑拆除,连同店堂前面的空地一道,扩建成焕然一新而又素朴古典,集中医、康养、茶室、展览和民宿为一体,名为“乡伴”的中医药馆,成为松阳“中医药复兴之地”一个新的标志。
善应堂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与佛教传人松阳密切相关。据有关史料,佛教于南朝梁时传人松阳,梁普通二年(521)在当时的县治(旌义乡旧市,今古市)南五里建妙善寺(后改名净因寺)以及现樟溪乡的灵岩寺(后名法昌寺);后陆续在紫荆村(今西屏街道)建立开善寺(后名法善、善因教寺)以及紫荆村西五里地的云龙寺(后改名延庆寺),当时松阳全县建有12个寺院。隋唐以后,佛教经久不衰,佛寺广筑。据《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记载,至清时,佛教在松阳最为兴盛,佛教寺庙达89座之多,禅院11座,庵堂52座。
以上史料所载的善因教寺,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松阳县志》载,建于梁大同四年(538),旧名开善寺,位于县西十五里,宋时改名法善寺。佛教讲究善有善报,因果报应,因此,元代年间又改名为善因教寺。唐贞元年间(785N805)县治从旌义乡旧市(今古市镇)迁至旧市以东二十华里地的紫荆村,为在新的县治传播和扩大佛教的影响,善因教寺也随县治的迁移,在新县治以南二华里地修建了善因堂。此时,与现人民大街形成丁字型东西向的市◇头和荷田岭下一带,是大溪(即松阴溪)的堤岸埠头,新建的善因堂坐北朝南,北面紧靠县治紫荆村,南面朝临清波荡漾的大溪,风光秀丽,佛音袅袅,尤其是做佛事时,为黎民百姓传来佛主保佑的佳音,因而民间称善因堂为“善音堂”。
古代我国各地的佛寺大多伴有塔的建立。塔是宗教建筑物,我国建塔是从佛教传人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佛教源于印度,塔也是从印度传来的。塔是用来保存埋藏在佛教徒看来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舍利的建筑物。为了表达对佛的虔诚信仰,信徒们争相供奉,于是保存舍利的建筑物———“塔”就应运而生。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国的塔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在用途上也有了许多发展和变化,超越单纯佛塔的限制,除了登高望远、獠望敌情、导航引渡和作为地区象征等等作用之外,民间还将其视作镇妖邪、镇水灾、镇天灾的神灵建筑。由于在松阳县治紫荆村西面不远处有座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历五年才建成的延庆寺塔,因此,善因堂僧人们也有此强烈的愿望,四出募捐筹建。明代洪武年间(1368B1398),松阳知县王彝(北平今北京人)在黎民百姓的捐助下,回应了善因堂僧人的要求,在善因堂西门外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高数寻”(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寻”)的砖塔,民间也称善音塔,与明清以来陆续建成的状元坊塔、仁寿坊塔、五福社塔、白塔、赤塔、延庆寺塔、青云塔等,形成松阳县治内外颇为壮观的“塔林”,佛教在古代松阳辉煌昌盛的情景可见一斑。
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曹立身(山西平定人)编、潘茂才(钱塘今杭州人)纂的《松阳县志》其中所列的“松阳全境图”标有“善音堂”和“善音塔”的图案,直到同治末年松阳知县支恒椿、丁风章等纂的光绪元年(1875)刊行的《松阳县志·卷四寺观》记载中才改为善应堂。所载文字摘于此:“善应堂在城南善观铺,道光二十五年毁,二十八年僧南昆募建”。
“善应堂者,供奉观音大士、文武二圣(即文圣孔子、武圣关公),神灵显赫,由来久矣”根据史料佐证,道光二十五年(1845)这一年,善音堂因遭特大火灾与整条街道两边的商店同时焚毁。三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寺僧四出募捐重建,县志中“僧南昆”是指后来的寺僧四出募捐,重建之后,仍为旧名的善音堂每年正月举办善音灯会,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同治年间,松阳先后有8任知县,最后一任是支恒椿(江苏省镇江丹徒人),任职10年,同治十三年(1874)在
任,根据他在任上写下的《善应堂砖塔记》(见光绪《松阳县志》)记载:“南街善应堂门外矗立一砖塔,高数寻,相传镇滔风焉”。“滔”读(yi″第二声)是“淫”的异体字,古时也说是“淫”的讹字,意思与“淫”字相同,“淫风”是一个词汇,释义为放荡的风俗。据此,令人不意臆测,明代松阳农耕经济发达,当时善应堂处于县治南城大溪埠头一带,经济交往、人员往来比较繁杂,社会风气可能不太如意,黎民百姓特别是僧人反映强烈,因此,洪武年间任松阳知县的王彝回应善因堂僧人的要求,在黎民百姓的捐助下,在善因堂外修建了“高数寻”的砖塔,以期达到“镇滔风焉”的目的。古时临水的地方都是繁华热闹之地,善应堂一带处于大溪边,也不乏称之为“滔风”的繁华绮丽之景象,据此,笔者也认为,明洪武年间在善因堂边修建砖塔,除了回应佛教徒的要求之外,县署还具有镇“滔风”之意。古时民间传说,松阳县邑之东大溪两边的青云山、横山经常会“走”在一起,造成大溪被阻断涨大水危及县邑。因此,同在明代200余年之后的万历年间(1573B1620),松阳知县林大佳(广西南宁市隆安县人)率民众在邑东十里外的青云山顶兴建青云塔(民间称“青蒙塔”),以此镇住“山怪”,使青云山不能“移走”,与横山不能“会龙”,保证大溪的畅通,也是同样的意思。
同治末年松阳知县支恒椿在其《善应堂砖塔记》中记载:“塔顶于二百年前(笔者注:即清康熙时期)因大风飞去,遂斜倚若醉汉,然历久不仆。”塔顶早已被风揭去,塔身也早已倾斜且摇摇晃晃,200余年之后到了同治七年,毕竟还是倒塌了。支恒椿用他知县的笔,记述了此砖塔神奇倒塌的情况:“同治七年(笔者注:1868)闰四月廿七日,突焉倾圮,其地屋舍如鳞,人烟稠密,幸而适仆于街衢之中央,以故不伤一人,不损一物,殆亦有神呵护之邑之人。苟能谋复其旧制,俾一邑中有贞无滔,非至幸欤。是为记。”善应塔突然轰然倒塌在屋舍如鳞,人烟稠密的街市,摇晃震裂的铃铛声杂乱哀鸣,显得格外凄惨。善应塔倒塌得很神奇,倒塌前没有一点先兆,突然间轰然倒塌在市◇头大街正中,不偏不倚砖块竟也未四处飞蹦,有神呵护似的,竟未伤及一人,也未毁坏一物。知县父母官因之感慨,也表达了他的愿望:如果能够谋求恢复修建,使县邑之中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是最大的幸事吗?可见,这个知县对任职地松阳深有感情、也是注重教化治理的好父母官。据有关史料,善应塔倒塌后,还出土了开元、太平、洪武时期的许多铜钱,县署将铜钱悉数救济给了周边穷苦的百姓。
善应塔神奇倒塌之后,松阳民间传闻四起,百姓惊叹于它突然轰然倒塌却未伤及百姓的生命财产,普遍认为,是多年来信佛念佛行善的报应,因此,民间又将善音堂说成了“善应堂”,寄寓了念佛行善、善有善报因果报应的佛理。而在同治十三年(1874)支恒椿任上亲任纂修,于光绪元年(1875)刊本的清光绪《松阳县志》,在其笔下代表官方正式记载时,响应百姓的心声,将“善音堂”改写为“善应堂”,作文时也明确题为《善应堂塔记》,而对列人县志中的“松阳县境图”堂和塔的位置上,仍然标注为“善音堂”和“善音塔”,可能是旧县志的沿袭,也可能寄寓着纪念之意。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善应堂还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寺庙,有数个僧人在此定居,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善应堂举行祭拜或佛事活动,虔诚信徒从附近的山野乡村赶来参加,因此,善应堂内常年香烟缭绕,烛光闪烁,人声鼎沸,钟声悠远。至今仍立在善应堂大门右侧的“善应堂碑”,立于民国廿一年(1932)岁次壬申小阳月,经理张秉正、何绍周、潘学文、叶岳溪、潘少浓,立碑人为:住持僧德祥。石碑高142公分、宽69公分,厚14公分,碑额“善应堂碑”四字为篆书,黑底石刻娟秀的楷书字体。据此记载:“本堂向有产业,以济香灯住持费用。先辈口口本属尽美,无如代远年湮者有之;拨人学校者有之;有寺僧者当后赎者又有之,此董事所以重新整顿,彻底清查,勒令僧人将现管账簿交出。董事再行将寺内田亩逐一踏明坛段租额,勒石竖碑,以垂久远于勿替云尔。”此石碑详细记载了当时以上董事经理逐一踏明后的善应堂的田亩产业及其租额收人,以确保“济香灯住持费用”,既是旧时松阳百姓虔诚信佛念佛的印证,更是善应堂历经时代风雨的见证。
民国时期,松阳县城初设社,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区,县城分36社。民国十七年(1928)分4里,十九年(1930)置镇,分东南西北4镇,之后不久,并为南北两镇。当时,为了县城消防安全和为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消防保障,县城徐汉佐(系我二伯公,族谱名徐履和,汉佐是字,另榜名友亮,谱载:“浙江第十一中学毕业,以作岁贡生,曾任松阳县高等小学正教员”)、潘春晨两位士绅发起组建县城消防队。民国廿九年(1940),原有的消防组织随之扩大,同时也随之拆分为南北两镇消防队,北镇消防队设在仙娘殿旧址(位于现太平坊西路,老西屏人民公社位置),南镇消防队则设在新建的善应堂内。
1944年起,松阳县城合并南北两镇,县城正式命名为西屏镇,设有义务消防组织,1951年4月直到松阳并人遂昌之前,县城建有消防总队,义务消防组织和总队队址就设在善应堂。直至1958年11月,松阳并人遂昌县之后,西屏镇从县城降为县直属镇,重新组建了西屏镇消防队,六十年代初期,队址由原北镇的仙娘殿旧址、原南镇的善应堂统一归并,改设到现横街10号房屋,善应堂这里就迎来了再次变身。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直到七十年代初,善应堂从原南镇消防队队址、县消防总队变身为西屏镇回收废旧物品的收购站。作为收购站的善应堂,厅堂里面正对门摆一张半旧的办公桌,办公桌旁边放着一个称重的磅,几张也是半旧不新的椅子,有时坐着一个装着一只假眼、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对我们小孩子来卖东西,总是瞄着那只假眼看我们,对我们也没有好态度,好像我们小孩都是偷来卖一样的,镇上的小孩们都不喜欢收购站这个人。而另一个个子高高、鼻梁也高高且红红的半老头,大家都叫他“赞赞叔公”的却很受我们小孩喜欢,我们小孩去卖东西,如果是卖旧报纸、厚纸板,他称过后会笑呵呵地夸我们几句,如果是卖铜锁、铁器之类东西,会问我们家里大人知道不,我们答不上,他就会和蔼地跟我们说,回去问问清楚可以卖再来。这家收购站也是当时西屏镇上唯一的一家,所以收购的废品很多,废旧报纸、厚纸板、铁器甚至鸡毛、鸭毛、猪骨头等等都有,堆满整个堂屋,堂屋内堆放的很满也很凌乱,有时,堂屋里堆放不下,就堆放在堂屋外面。那时,好象也没有什么卫生城镇、文明城镇之说,收购站如此堆放,镇上也熟视无睹,特别是年节前鸡毛、鸭毛、猪骨头收得多了,难免有一股股呛鼻的气味弥漫在善应堂四周,镇上的人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可能是收购站堆七杂八,有时连收购站外都被收购来的物品堆得很杂乱,在大街上毕竟不雅观,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约是在1970年下半年,收购站搬迁到了不远处的水牵面弄内。
1971年元月起,善应堂由此变身为国营西屏中西药商店。西屏镇唯一的这家药店,原是中药、西药分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公私合营”之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太平坊下现人民大街97号(现志远牙科诊所)二间和下面隔一扇门户紧连的一间现为香发廊共三间店面,是纯中药店,店名就叫国营西屏中药店。六十年代后期在此中药店稍往下不远、现太平坊下人民大街105号(现小杨五金店)二间和下面紧连的大运金行一间,共三间店面开设西药店。直到七十年代初,中西药两店合并搬迁到善应堂。从大门进人略显正方形偌大的厅堂,柜台的摆置是倒凹字的格局:厅堂左边为西药柜台,右边和中间为中药柜台,厅堂后面也比较宽大的屋内放置一些药材,同时也是切药的工场。原来的经理、军转干部赵瑞松“靠边站”(“文革”时的俗语,意为虽未打倒却已被夺权),药店雇工出身的程龙根时为负责人,主持了搬迁。
国营西屏中西药店搬迁到善应堂之后不久,正是“文革”动乱过后社会秩序渐趋恢复的时期,当时城乡普遍缺医少药,“坐堂医师”“土郎中”“土中医”作为“封建余孽”被取缔,代之而起的是“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受到格外的重视。各级各地“革委会”大力贯彻落实毛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和“用心寻找当地群众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的指示精神,普及中草药知识,推广中草药的应用,推进合作医疗和在城乡普遍实行“赤脚医生”为当地百姓治病,一时成为上级的要求和全社会的热潮。七十年代初,遂昌县也成立了“遂昌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卫生办公室中草药研究推广小组”,根据上级要求,国营西屏中西药商店负责筹办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务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从紧邻善应堂药店南侧的一蔡姓人家租来店面正朝人民大街的三间店堂(即现在的淑慧理发店),开办了“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务部”(松阳百姓俗称“善应堂草药店”)。善应堂中草药推广服务部开了三年左右,可能是善应堂药店店堂比较宽绰,为节约房租开支,关门退租,关门却不歇业,继而在善应堂药店最中间的位置,开辟了草药专柜,推广普及和为百姓提供草药的服务。这样,善应堂药店就形成了左右两边仍分别是中西药业务,中间是草药业务的格局,又成了西屏镇唯一的集中药、西药和草药为一家的药店,店名改为“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
1978年下半年,“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改名为“遂昌县医药公司松阳商店”。直到1982年春季,松阳恢复县建制之后,在松阳医药商店基础上,组建松阳县医药公司。在西屏镇区钟楼路以北、人民大街以东,有10余幢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字结构的二层砖墙建筑,是原遂昌县商业局属下的百货、医药、食品、土产等公司的松阳仓库,松阳县医药公司组建时,就将建在这里的仓库改建成公司的办公场所,公司临大街的店面(现人民大街日用品批发商店)开设药店,由国营西屏中西药综合商店经营,原在善应堂药店工作的所有职员,属国营编制悉数到此工作,而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开设在善应堂的药店,改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由新招进的集体编制的员工经营,之后,承包、改制,继而转为个人承包,经营性质虽历经变化,而善应堂药店始终在松阳百姓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药店和其他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一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的松阳县城药店远不止善应堂一家独有,不同名称的药店已有几十家,而善应堂药店尽管从人民大街154号搬迁至人民大街129号,始终是松阳古城医药行业中的金牌老字号;与之伴生的善应堂草药店,虽然早早淡出人们视野,其在推广普及和为百姓提供草药服务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松阳县城如今遍布涌现的草药店、草药铺中,似乎也足以得到印证。
善应堂药店和古来有之的善应堂地名,几乎成了同一概念,是松阳古老县城极富地方特色文化底蕴的所在。如今,善应堂药店拆旧新建为松阳中医药馆,充分体现了松阳古老文化和历史悠久的中医药业的传承,当为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