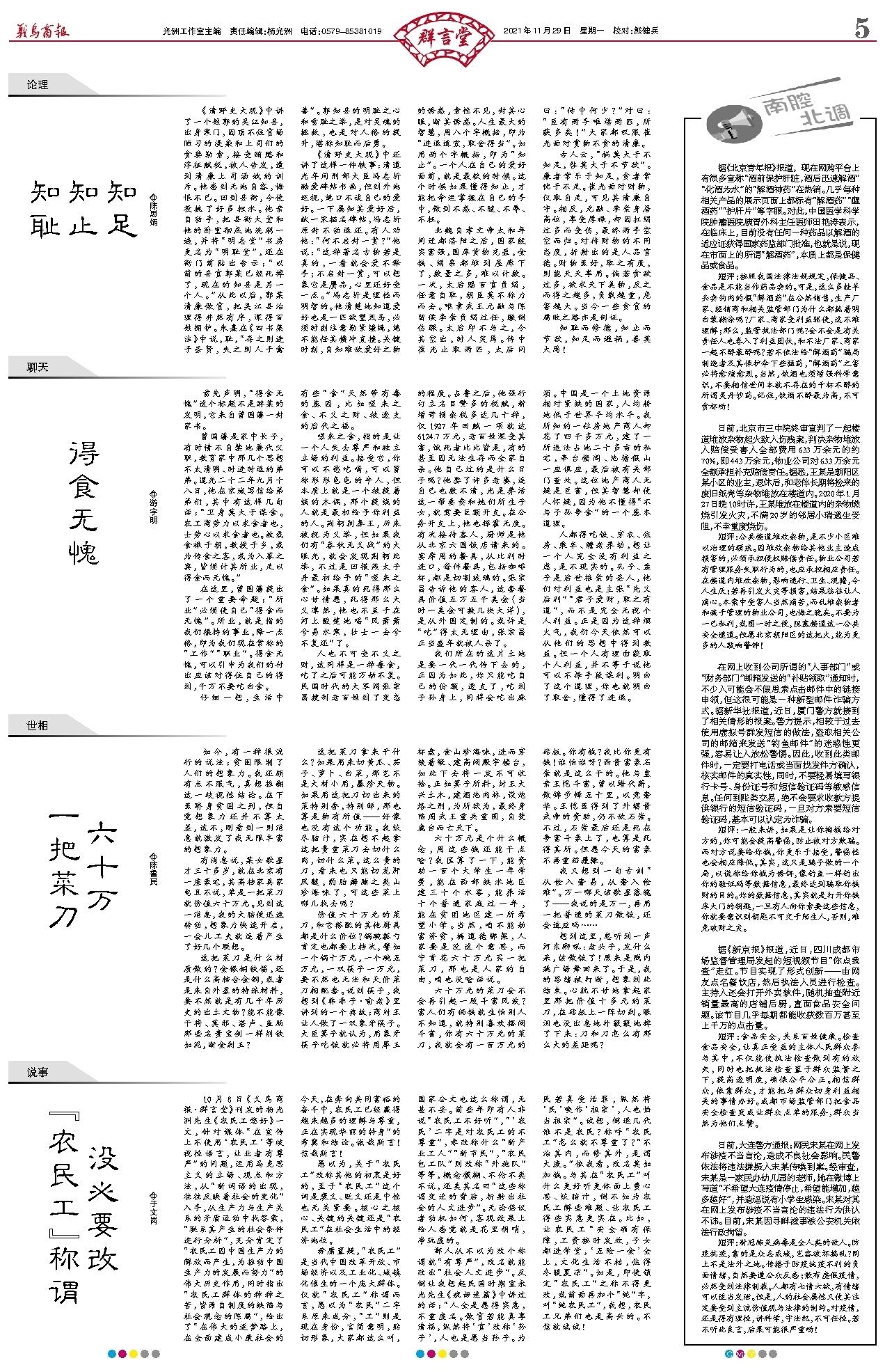10月8日《义乌商报·群言堂》刊发的杨光洲先生《农民工您好》一文,针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新词语的出现,往往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入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找答案,“联系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农民工因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而产生,为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努力”的伟大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农民工群体的种种之苦,皆源自制度的缺陷与社会观念的陈腐”,给出了“在伟大的逐梦路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奋斗中,农民工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尊重,正在实现华丽的转身”的希冀和结论。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愚以为,关于“农民工”改称其他的初衷是好的,至于“农民工”这个词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也无关紧要。核心之核心、关键的关键还是“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地位。
毋庸置疑,“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催生的一个庞大群体。仅就“农民工”称谓而言,愚以为“农民”二字系原来成分,“工”则是现在身份,言简意明,贴切形象,大家都这么叫,国家公文也这么称谓,无甚不妥。前些年即有人非说“农民工不好听”,“‘农民’二字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非改称什么“新产业工人”“新市民”,“农民包工队”则改称“外施队”等等,概念模糊、不伦不类不说,还美其名曰“这些称谓变迁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的人文进步”。无论倡议者动机如何,客观效果上给人感觉就是花里胡哨,净玩虚的。
鄙人从不以为改个称谓就“有尊严”,改名就能改出“社会人文进步”。反倒让我想起民国时期宣永光先生《疯话连篇》中讲过的话:“人全是愿得实惠,不重虚名。做官若能真享清福,纵然将‘官’改称‘孙子’,人也是愿当孙子。为民若真受活罪,纵然将‘民’唤作‘祖宗’,人也怕当祖宗”。试想,倒退几代谁不是农民?称呼“农民工”怎么就不尊重了?“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依我看,改名莫如加钱。与其在“农民工”叫什么更好听更体面上费心思、绞脑汁,倒不如为农民工解些难题、让农民工得些实惠更实在。比如,让农民工“安全确有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子女都进学堂,‘五险一金’全上,文化生活不枯,住得冬暖夏凉”。如是,即使锁定“农民工”之称不得更改,或前面再加个“纯”字,叫“纯农民工”,我想,农民工兄弟们也是高兴的。不信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