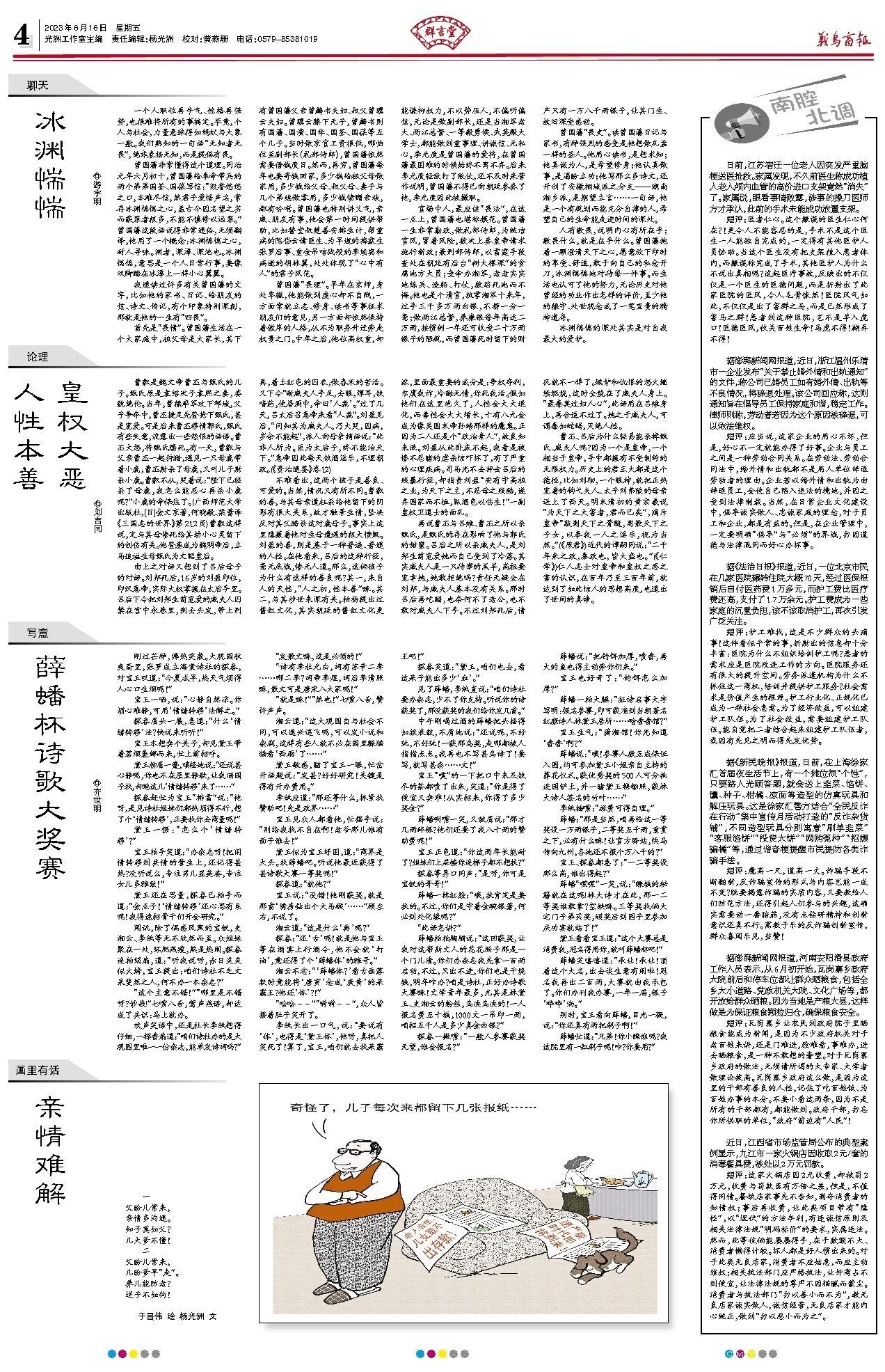一个人职位再牛气、性格再强势,也很难将所有的事搞定。毕竟,个人与社会,力量悬殊得如蚂蚁与大象一般。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绝非表扬无知,而是提倡有畏。
曾国藩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曾国藩给奉命带兵的两个弟弟国荃、国葆写信:“毁誉悠悠之口,本难尽信,然君子爱惜声名,常存冰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这段话说得非常通俗,无须翻译,他用了一个概念:冰渊惴惴之心,耐人寻味。渊者,深潭、深池也。冰渊惴惴,意思是一个人日常行事,要像双脚踏在冰潭上一样小心翼翼。
我通读过许多有关曾国藩的文字,比如他的家书、日记、给朋友的信、诗文、传记,有个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他的一生有“四畏”。
首先是“畏情”。曾国藩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祖父母是大家长,其下有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夫妇、叔父曾骥云夫妇。曾骥云膝下无子,曾麟书则有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等五个儿子。当时做京官工资很低,哪怕位至副部长(礼部侍郎),曾国藩依然需要借钱度日。然而,再穷,曾国藩每年也要寄钱回家,多少钱给祖父母做家用,多少钱给父母、叔父母、妻子与几个弟媳做零用,多少钱馈赠亲族,都有吩咐。曾国藩也特别讲义气,亲戚、朋友有事,他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比如替堂叔楚善安排生计,帮重病的陈岱云请医生、为早逝的梅霖生张罗后事、重金吊唁战殁的李续宾和病逝的胡林翼,处处体现了“心中有人”的君子风范。
曾国藩“畏理”。早年在京师,身处卑微,他能做到虚心却不自贱,一方面常就立志、修身、读书等事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却依然保持着傲岸的人格,从不为职务升迁奔走权贵之门。中年之后,他位高权重,却能谦抑权力,不以势压人,不偏听偏信,无论是做副部长,还是当湘军老大、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都能做到重事理、讲诚信、无私心。李元度是曾国藩的爱将,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后来李元度轻敌打了败仗,还不及时来营作说明,曾国藩不得已向朝廷参奏了他,李元度因此被撤职。
官场中人,最应该“畏法”,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也堪称模范。曾国藩一生非常勤政,做礼部侍郎,为纯洁官风,冒着风险,数次上奏皇帝请求施行新政;兼刑部侍郎,以雷霆手段查处在朝廷有后台“树大根深”的贪腐地方大员;受命办湘军,老老实实地练兵、造船、打仗,数蹈死地而不悔。他也是个清官,执掌湘军十来年,过手三千多万两白银,不捞一分一毫;做两江总督,养廉银每年高达二万两,按惯例一年还可收受二十万两银子的陋规,而曾国藩死时留下的财产只有一万八千两银子,让其门生、故旧深受感动。
曾国藩“畏史”。读曾国藩日记与家书,有种强烈的感受是他想做孔孟一样的圣人。他用心读书,是想求知;他真诚为人,是希望修身;他认真做事,是渴盼立功;他写那么多诗文,还开创了安徽桐城派之分支——湖南湘乡派,是期望立言……一句话,他是一个有规划而能充分自律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能走进时间的深处。
人有敬畏,说明内心有所在乎;敬畏什么,就是在乎什么。曾国藩抱着一颗澄清天下之心,愿意放下即时的享受、舒适,敢于向自己的私念开刀,冰渊惴惴地对待每一件事。而生活也认可了他的努力,无论历史对他曾经的功业作出怎样的评价,至少他的操守、处世观念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存。
冰渊惴惴的深处其实是对自我最大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