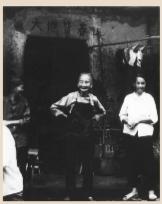汪祖军
华埠人讲话,基本上语速都比较快,跟大队会计拨算盘一样,噼里啪啦直来直去,比如我。好比乡下的土狗,精骨痨瘦却不失勇武。
华埠人讲话,似乎包含华埠人的性格和情感。节奏强劲时,如连日暴雨后那浪花飞溅的山洪声;节奏舒缓时,如盛夏午后悠闲散步的过堂风。
华埠人的勤劳、善良、坦诚,使华埠话具有明显的朴实性、直爽性和趣味性。一些特定情形的形容和描述,用华埠话讲起来那是相当的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有的以人说理,有的以物喻情,既简明通俗,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一
“某某,你与赞(现在)怎么会蒋(这样)滚壮的啊”;“你再蒋(这样)死不烂像,我都懒得什(理)你了”;“昨晚看得那部电影危险危险(非常非常)赞”“你这个银(人)切(喝)酒怎么跟妇女一样滴”。这些话虽然粗俗但是形象,就好比吃羊肉必有膻味,吃鱼就必带腥气。
你与某人讲有个美女很漂亮,哪怕漂亮得倾城倾国,他或许无动于衷,因为这是抽象表达;如果你马上拉这个美女深情款款地向他走去,他僵硬的脸肯定会生动起来,这就是形象的魅力。
华埠话,只要你仔细观察认真听,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喜欢加前缀和后缀,来强调语意。华埠话讲“冷”不用“冷”,是用“冰吧冷”,多了“冰吧”两个字,加深了冷的程度;讲开水很“烫”不用“烫”,是用“博勒滚”,“博勒滚”这一拟声词让人马上联想到水烧开后沸腾的情景;讲“湿”不用“湿”,是用“偷巴歇”;讲“黑”不用“黑”,是用“漆吧乌”;讲“大”不用“大”,是用“满大过”;讲“白”不用“白”,是用“雪白”;讲“陡”不用“陡”,是用“笔许”……
形象生动,一针见血,一些话听后能让人不得不佩服先人们的“智慧”。说某人靠不住,或不堪委以重任,会说“叫他做事,托鬼医病”;说某件事情没什么可商量的,会说“三两棉花,步不得弹(不用谈)”;说某人不可理喻很难打交道,会说“跟他谈天,勒色(垃圾)桶里切(抽)香烟、尿壶里打电话”;说某人做事情拖拖拉拉,会说“这个人做事情太摸(拖拉)了,老虎赶来他还要看下公的母的”……
二
那一年,我还在燃料公司上班。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请问某科长在吗”,“不好意思,他不在歪——”,“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那我不晓得歪——”。一旁的同事说我的华埠话真好听,特别是后面的那个“歪”字,有着戏曲的腔调,像幽深的弄堂一样绵长曲折。既没有“他不在”“不晓得”那种生硬冷漠的语气,又有当事人不在的遗憾和爱莫能助的愧疚。
我是地地道道的华埠人,华埠话就像娘胎里带来的胎记渗透到了骨子里,虽然经过几十年风雨的洗礼,仍然改变不了语音的底蕴。也难怪,每当我在一些场合“熟练”地操起普通话时,立马就会有人问起:“你是华埠人吧?”那神情,由不得我不马上点头承认。
外地来华埠作客的朋友或者来华埠经商的人,都说华埠话跟普通话差不多,而华埠话的易懂是有道理的。
据《华埠镇志》的注释,华埠自宋以来,就是浙、晥、赣三省七县水陆重要的交通枢纽,素有“钱江源头第一埠”的美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外省、外县的人来此经商和营生,一度被冠以“小上海”之美称。据统计,华埠镇居民就有来自19省159县187个姓氏的人。方言不仅有徽语、赣语,也有衢州话、严州话、闽南话、金华话和新安江话等。
这些人,从各个不同的时期、各个不同的地方、带着各自家乡的方言聚集在华埠,大家相互间需要交往,需要沟通。经商贸易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不得不互相学习、渗透、改造、借鉴、融通。于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自然而然地演变并形成今天这种具有地方特色、各方区域都能听懂、接受、理解和运用的方言——华埠话。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同学之间交流的都是华埠话,偶尔有一两个同学说普通话,也是转学来的,课堂上虽然都是普通话,也很少有人因为字音讲得不准或讲错,而去追究或帮助更正。因为老师基本上也是属于“半桶水”。到了我儿子女儿这一代,在家里或学校课堂上,都是以普通话交流了,华埠话倒成了陌生的语言。虽然我的儿女都是土生土长的华埠人,但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华埠话就像断了腿一样,软踏踏的,很多俏皮话都不会说了。
三
以前,因为贫穷闭塞,区域之间交流少,牛郎织女也不多,普通话使用的频率不高,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需求不强烈。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受益”人群已经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了。
如今,当听到讲了大半辈子华埠话的大伯大妈、爷爷奶奶们用蹩脚的普通话跟孙辈交流时,我总觉得就像隔着一层玻璃,彼此看起来很近,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如同两张飘落的树叶,虽然来自同一个地方,却不知道是不是同根生。
如今的华埠话,犹如昨日黄花,正在逐渐凋零。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或是异地联姻。即使华埠话还有一定的市场,基本上都是以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老华埠人为主,年轻的人则开始习惯使用普通话。比如“扁食、夺悬、欠窗、钢勾、得伟、马德克等等”,现在都改叫“馄饨、突然、窗门、蜻蜓、故意、摩托车”。
这些年,我似乎看到那亲切的华埠话正在握手告别,同时告别的还有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祖辈们早作夜息、薪火相传的风俗人情,还有那些传统小吃、民俗民风等乡土文化,还有人们诙谐幽默、苦中作乐的积极向上精神以及邻里之间、亲朋好友相互帮衬的传统美德。
司空见惯的东西,反而最容易被人视而不见。当有朝一日静下心来细心琢磨每天说过的话时,才发现家乡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更是千百年来祖上遗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卫防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