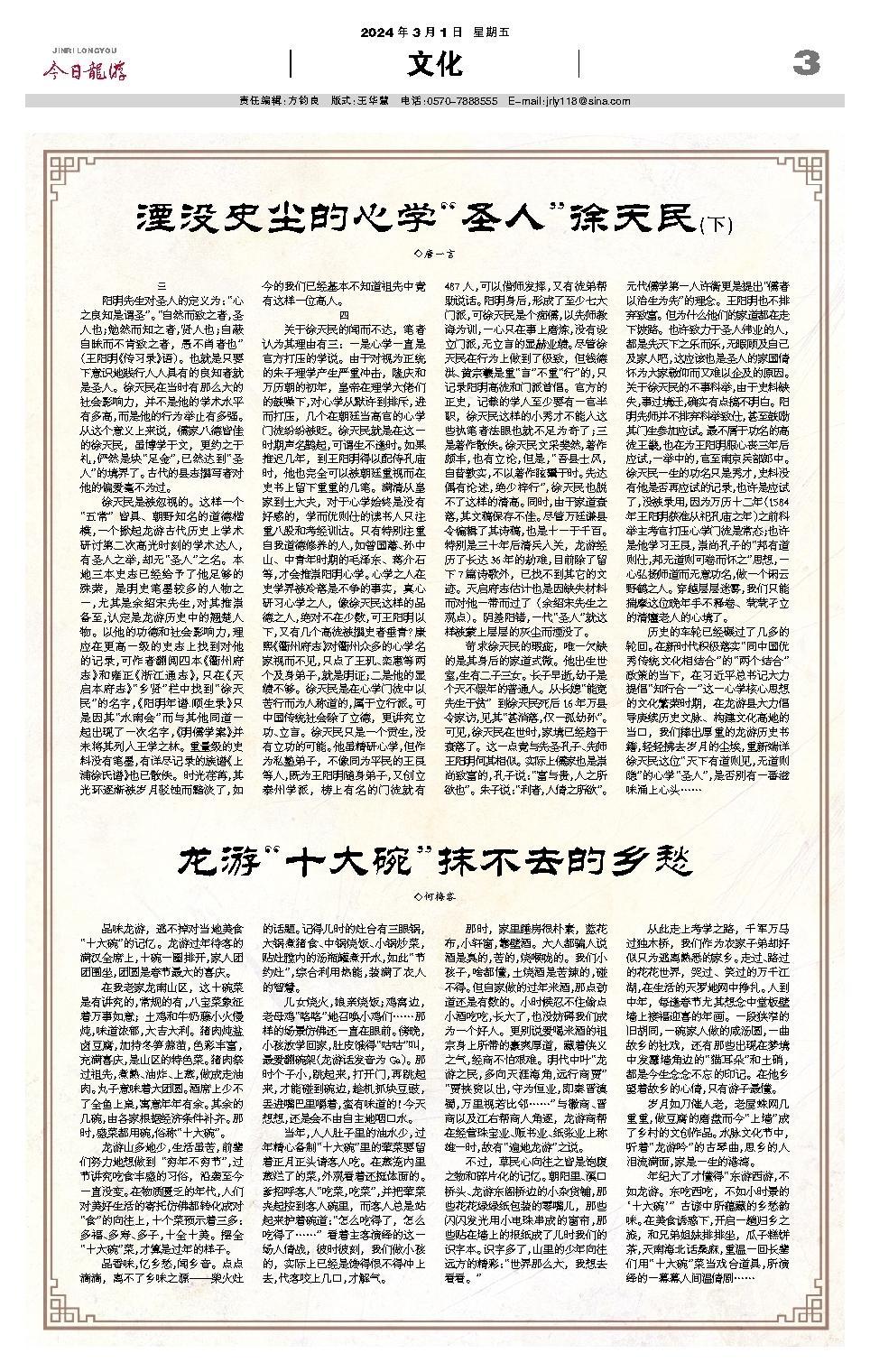◇何梅容
品味龙游,逃不掉对当地美食“十大碗”的记忆。龙游过年待客的满汉全席上,十碗一圈排开,家人团团围坐,团圆是春节最大的喜庆。
在我老家龙南山区,这十碗菜是有讲究的,常规的有,八宝菜象征着万事如意;土鸡和牛奶藤小火慢炖,味道浓郁,大吉大利。猪肉炖盐卤豆腐,加持冬笋蒜苗,色彩丰富,充满喜庆,是山区的特色菜。猪肉祭过祖先,煮熟、油炸、上蒸,做成走油肉。丸子意味着大团圆。酒席上少不了全鱼上桌,寓意年年有余。其余的几碗,由各家根据经济条件补齐。那时,盛菜都用碗,俗称“十大碗”。
龙游山多地少,生活虽苦,前辈们努力地想做到“穷年不穷节”,过节讲究吃食丰盛的习俗,沿袭至今一直没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仿佛都转化成对“食”的向往上,十个菜预示着三多:多福、多寿、多子,十全十美。摆全“十大碗”菜,才算是过年的样子。
品香味,忆乡愁,闻乡音。点点滴滴,离不了乡味之源——柴火灶的话题。记得儿时的灶台有三眼锅,大锅煮猪食、中锅烧饭、小锅炒菜,贴灶膛内的汤瓶罐煮开水,如此“节约灶”,综合利用热能,装满了农人的智慧。
儿女烧火,娘亲烧饭;鸡窝边,老母鸡“咯咯”地召唤小鸡们……那样的场景仿佛还一直在眼前。傍晚,小孩放学回家,肚皮饿得“咕咕”叫,最爱翻碗架(龙游话发音为Ga)。那时个子小,跳起来,打开门,再跳起来,才能碰到碗边,趁机抓块豆豉,丢进嘴巴里嚼着,蛮有味道的!今天想想,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咽口水。
当年,人人肚子里的油水少,过年精心备制“十大碗”里的荤菜要留着正月正头请客人吃。在蒸笼内里蒸烂了的菜,外观看着还挺体面的。爹招呼客人“吃菜,吃菜”,并把荤菜夹起按到客人碗里,而客人总是站起来护着碗道:“怎么吃得了,怎么吃得了……”看着主客演绎的这一场人情战,彼时彼刻,我们做小孩的,实际上已经是馋得恨不得冲上去,代客咬上几口,才解气。
那时,家里睡房很朴素,蓝花布,小轩窗,靠壁酒。大人都骗人说酒是臭的,苦的,烧喉咙的。我们小孩子,啥都懂,土烧酒是苦辣的,碰不得。但自家做的过年米酒,那点劲道还是有数的。小时候忍不住偷点小酒吃吃,长大了,也没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更别说爱喝米酒的祖宗身上所带的豪爽厚道,藏着侠义之气,经商不怕艰难。明代中叶“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帮商人角逐,龙游商帮在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上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说。
不过,草民心向往之皆是饱腹之物和碎片化的记忆。朝阳里、溪口桥头、龙游东阁桥边的小杂货铺,那些花花绿绿纸包装的零嘴儿,那些闪闪发光用小电珠串成的窗帘,那些贴在墙上的报纸成了儿时我们的识字本。识字多了,山里的少年向往远方的精彩:“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从此走上考学之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作为农家子弟却好似只为逃离熟悉的家乡。走过、路过的花花世界,哭过、笑过的万千江湖,在生活的天罗地网中挣扎。人到中年,每逢春节尤其想念中堂板壁墙上接福迎喜的年画。一段狭窄的旧胡同,一碗家人做的咸汤圆,一曲故乡的社戏,还有那些出现在梦境中发霉墙角边的“猫耳朵”和土硝,都是今生念念不忘的印记。在他乡望着故乡的心情,只有游子最懂。
岁月如刀催人老,老屋蛛网几重重,做豆腐的磨盘而今“上墙”成了乡村的文创作品。水脉文化节中,听着“龙游吟”的古琴曲,思乡的人泪流满面,家是一生的港湾。
年纪大了才懂得“东游西游,不如龙游。东吃西吃,不如小时景的‘十大碗’”古谚中所蕴藏的乡愁韵味。在美食诱惑下,开启一趟归乡之旅,和兄弟姐妹排排坐,瓜子糕饼茶,天南海北话桑麻,重温一回长辈们用“十大碗”菜当戏台道具,所演绎的一幕幕人间温情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