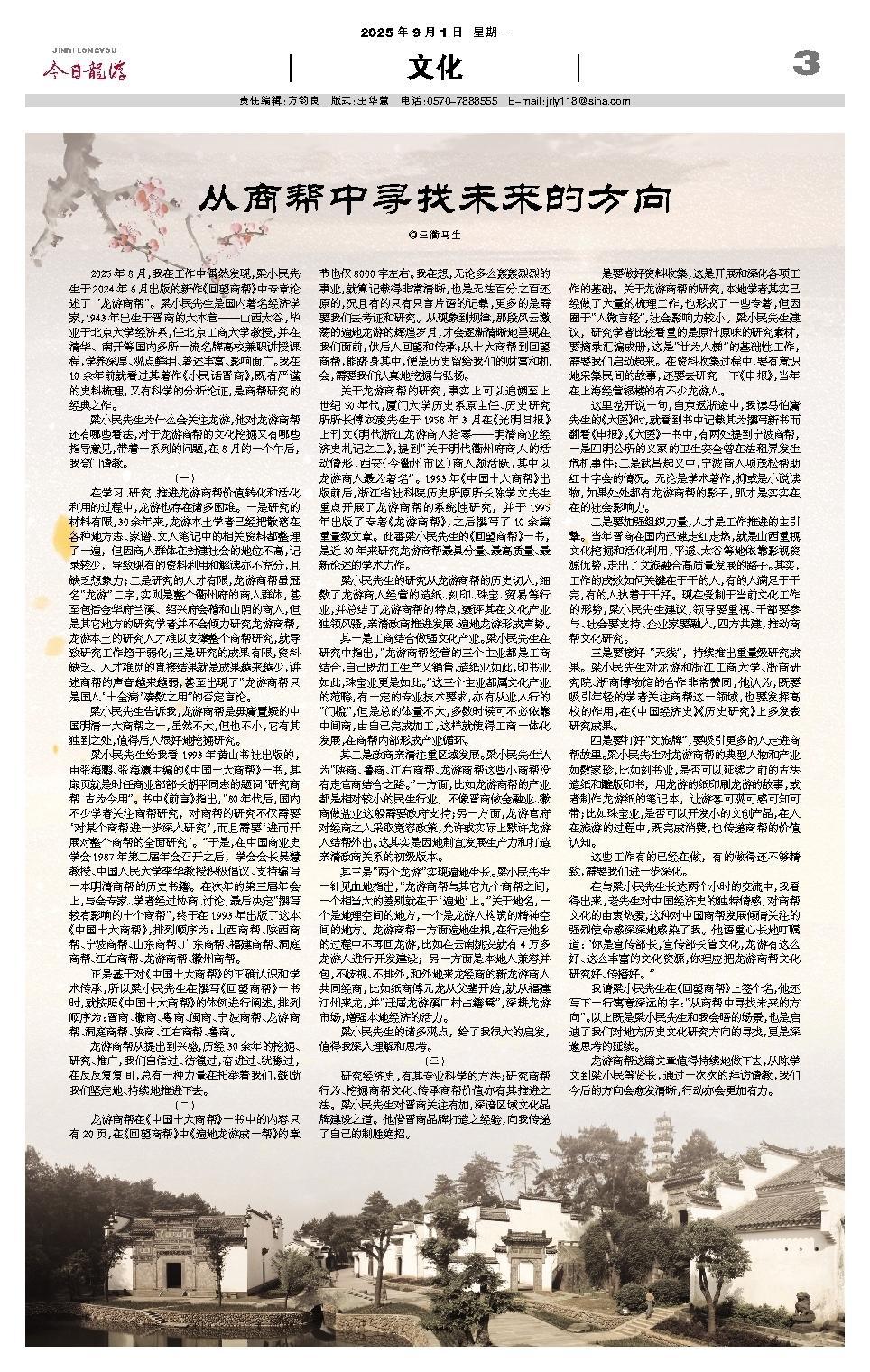◎三衢马生
2025年8月,我在工作中偶然发现,梁小民先生于2024年6月出版的新作《回望商帮》中专章论述了“龙游商帮”。梁小民先生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晋商的大本营——山西太谷,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并在清华、南开等国内多所一流名牌高校兼职讲授课程,学养深厚、观点鲜明、著述丰富、影响面广。我在10余年前就看过其著作《小民话晋商》,既有严谨的史料梳理,又有科学的分析论证,是商帮研究的经典之作。
梁小民先生为什么会关注龙游,他对龙游商帮还有哪些看法,对于龙游商帮的文化挖掘又有哪些指导意见,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在8月的一个午后,我登门请教。
(一)
在学习、研究、推进龙游商帮价值转化和活化利用的过程中,龙游也存在诸多困难。一是研究的材料有限,30余年来,龙游本土学者已经把散落在各种地方志、家谱、文人笔记中的相关资料都整理了一遍,但因商人群体在封建社会的地位不高,记录较少,导致现有的资料利用和解读亦不充分,且缺乏想象力;二是研究的人才有限,龙游商帮虽冠名“龙游”二字,实则是整个衢州府的商人群体,甚至包括金华府兰溪、绍兴府会稽和山阴的商人,但是其它地方的研究学者并不会倾力研究龙游商帮,龙游本土的研究人才难以支撑整个商帮研究,就导致研究工作趋于弱化;三是研究的成果有限,资料缺乏、人才难觅的直接结果就是成果越来越少,讲述商帮的声音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龙游商帮只是国人‘十全病’凑数之用”的否定言论。
梁小民先生告诉我,龙游商帮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之一,虽然不大,但也不小,它有其独到之处,值得后人很好地挖掘研究。
梁小民先生给我看1993年黄山书社出版的,由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其扉页就是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的题词“研究商帮 古为今用”。书中《前言》指出,“80年代后,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商帮研究,对商帮的研究不仅需要‘对某个商帮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需要‘进而开展对整个商帮的全面研究’。”于是,在中国商业史学会1987年第二届年会召开之后,学会会长吴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积极倡议、支持编写一本明清商帮的历史书籍。在次年的第三届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经过协商、讨论,最后决定“撰写较有影响的十个商帮”,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这本《中国十大商帮》,排列顺序为: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
正是基于对《中国十大商帮》的正确认识和学术传承,所以梁小民先生在撰写《回望商帮》一书时,就按照《中国十大商帮》的体例进行阐述,排列顺序为: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陕商、江右商帮、鲁商。
龙游商帮从提出到兴盛,历经30余年的挖掘、研究、推广,我们自信过、彷徨过,奋进过、犹豫过,在反反复复间,总有一种力量在托举着我们,鼓励我们坚定地、持续地推进下去。
(二)
龙游商帮在《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的内容只有20页,在《回望商帮》中《遍地龙游成一帮》的章节也仅8000字左右。我在想,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就算记载得非常清晰,也是无法百分之百还原的,况且有的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考证和研究。从现象到规律,那段风云激荡的遍地龙游的辉煌岁月,才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供后人回望和传承;从十大商帮到回望商帮,能跻身其中,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和机会,需要我们认真地挖掘与弘扬。
关于龙游商帮的研究,事实上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傅衣凌先生于1958年3月在《光明日报》上刊文《明代浙江龙游商人拾零——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二》,提到“关于明代衢州府商人的活动情形,西安(今衢州市区)商人颇活跃,其中以龙游商人最为著名”。1993年《中国十大商帮》出版前后,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陈学文先生重点开展了龙游商帮的系统性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专著《龙游商帮》,之后撰写了10余篇重量级文章。此番梁小民先生的《回望商帮》一书,是近30年来研究龙游商帮最具分量、最高质量、最新论述的学术力作。
梁小民先生的研究从龙游商帮的历史切入,细数了龙游商人经营的造纸、刻印、珠宝、贸易等行业,并总结了龙游商帮的特点,褒评其在文化产业独领风骚,亲清政商推进发展、遍地龙游形成声势。
其一是工商结合做强文化产业。梁小民先生在研究中指出,“龙游商帮经营的三个主业都是工商结合,自己既加工生产又销售,造纸业如此,印书业如此,珠宝业更是如此。”这三个主业都属文化产业的范畴,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要求,亦有从业入行的“门槛”,但是总的体量不大,多数时候可不必依靠中间商,由自己完成加工,这样就使得工商一体化发展,在商帮内部形成产业循环。
其二是政商亲清注重区域发展。梁小民先生认为“陕商、鲁商、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这些小商帮没有走官商结合之路。”一方面,比如龙游商帮的产业都是相对较小的民生行业,不像晋商做金融业、徽商做盐业这般需要政府支持;另一方面,龙游官府对经商之人采取宽容政策,允许或实际上默许龙游人结帮外出。这其实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和打造亲清政商关系的初级版本。
其三是“两个龙游”实现遍地生长。梁小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龙游商帮与其它九个商帮之间,一个相当大的差别就在于‘遍地’上。”关于地名,一个是地理空间的地方,一个是龙游人构筑的精神空间的地方。龙游商帮一方面遍地生根,在行走他乡的过程中不再回龙游,比如在云南姚安就有4万多龙游人进行开发建设;另一方面是本地人兼容并包,不歧视、不排外,和外地来龙经商的新龙游商人共同经商,比如纸商傅元龙从父辈开始,就从福建汀州来龙,并“迁居龙游溪口村占籍焉”,深耕龙游市场,增强本地经济的活力。
梁小民先生的诸多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值得我深入理解和思考。
(三)
研究经济史,有其专业科学的方法;研究商帮行为、挖掘商帮文化、传承商帮价值亦有其推进之法。梁小民先生对晋商关注有加,深谙区域文化品牌建设之道。他借晋商品牌打造之经验,向我传递了自己的制胜绝招。
一是要做好资料收集,这是开展和深化各项工作的基础。关于龙游商帮的研究,本地学者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梳理工作,也形成了一些专著,但因囿于“人微言轻”,社会影响力较小。梁小民先生建议,研究学者比较看重的是原汁原味的研究素材,要摘录汇编成册,这是“甘为人梯”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我们启动起来。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要有意识地采集民间的故事,还要去研究一下《申报》,当年在上海经营银楼的有不少龙游人。
这里岔开说一句,自京返浙途中,我读马伯庸先生的《大医》时,就看到书中记载其为撰写新书而翻看《申报》。《大医》一书中,有两处提到宁波商帮,一是四明公所的义冢的卫生安全曾在法租界发生危机事件;二是武昌起义中,宁波商人项茂松帮助红十字会的情况。无论是学术著作,抑或是小说读物,如果处处都有龙游商帮的影子,那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要加强组织力量,人才是工作推进的主引擎。当年晋商在国内迅速走红走热,就是山西重视文化挖掘和活化利用,平遥、太谷等地依靠影视资源优势,走出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其实,工作的成效如何关键在于干的人,有的人满足于干完,有的人执着于干好。现在受制于当前文化工作的形势,梁小民先生建议,领导要重视、干部要参与、社会要支持、企业家要融入,四方共建,推动商帮文化研究。
三是要接好“天线”,持续推出重量级研究成果。梁小民先生对龙游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浙商博物馆的合作非常赞同,他认为,既要吸引年轻的学者关注商帮这一领域,也要发挥高校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史》《历史研究》上多发表研究成果。
四是要打好“文旅牌”,要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商帮故里。梁小民先生对龙游商帮的典型人物和产业如数家珍,比如刻书业,是否可以延续之前的古法造纸和雕版印书,用龙游的纸印刷龙游的故事,或者制作龙游纸的笔记本,让游客可观可感可知可带;比如珠宝业,是否可以开发小的文创产品,在人在旅游的过程中,既完成消费,也传递商帮的价值认知。
这些工作有的已经在做,有的做得还不够精致,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
在与梁小民先生长达两个小时的交流中,我看得出来,老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的独特情感,对商帮文化的由衷热爱,这种对中国商帮发展倾情关注的强烈使命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你是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管文化,龙游有这么好、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你理应把龙游商帮文化研究好、传播好。”
我请梁小民先生在《回望商帮》上签个名,他还写下一行寓意深远的字:“从商帮中寻找未来的方向”。以上既是梁小民先生和我会晤的场景,也是启迪了我们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向的寻找,更是深邃思考的延续。
龙游商帮这篇文章值得持续地做下去,从陈学文到梁小民等贤长,通过一次次的拜访请教,我们今后的方向会愈发清晰,行动亦会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