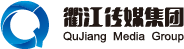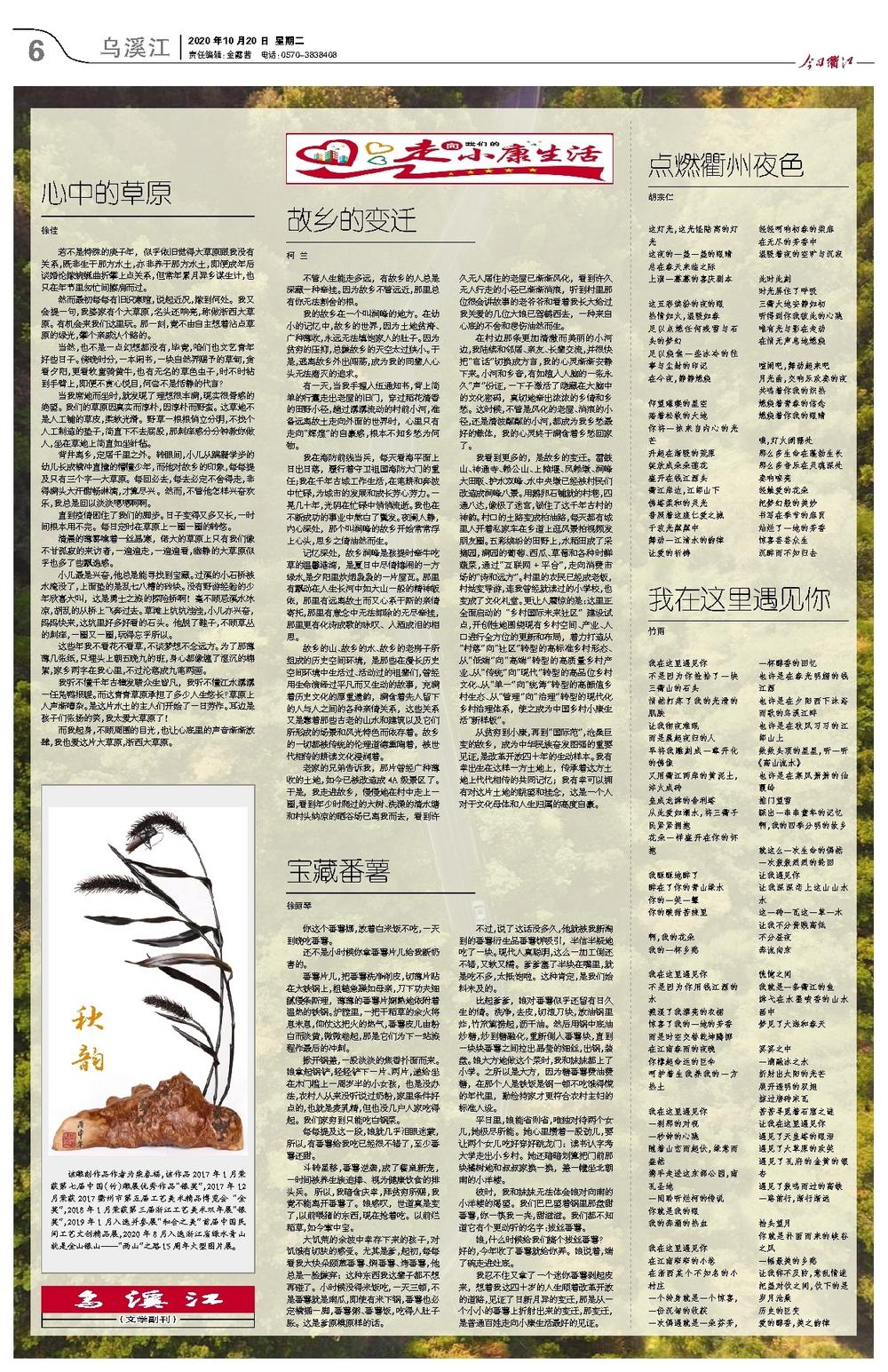柯 兰
不管人生能走多远,有故乡的人总是深藏一种牵挂。因为故乡不管远近,那里总有你无法割舍的根。
我的故乡在一个叫涧峰的地方。在幼小的记忆中,故乡的世界,因为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永远无法填饱家人的肚子。因为贫穷的压抑,总嫌故乡的天空太过狭小。于是,逃离故乡外出闯荡,成为我的同辈人心头无法磨灭的追求。
有一天,当我手握入伍通知书,背上简单的行囊走出老屋的旧门,穿过稻花清香的田野小径,趟过潺潺流动的村前小河,准备远离故土走向外面的世界时,心里只有走向“辉煌”的自豪感,根本不知乡愁为何物。
我在海防前线当兵,每天看海平面上日出日落,履行着守卫祖国海防大门的重任;我在千年古城工作生活,在笔耕和奔波中忙碌,为城市的发展和成长劳心劳力。一晃几十年,光阴在忙碌中悄悄流逝。我也在不断成功的事业中熬白了鬓发。夜阑人静,内心深处,那个叫涧峰的故乡开始常常浮上心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记忆深处,故乡涧峰是孩提时牵牛吃草的温馨港湾,是夏日中尽情嬉闹的一方绿水,是夕阳里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那里有飘动在人生长河中如大山一般的精神皈依,那里有远离故土而又心系于斯的亲情寄托,那里有意念中无法卸除的无尽牵挂,那里更有化诗成歌的咏叹、入酒成泪的相思。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老房子所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是那些在漫长历史空间环境中生活过、活动过的祖辈们,曾经用生命演绎过平凡而又生动的故事,充满着历史文化的厚重遗韵,满含着先人留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亲情关系,这些关系又是靠着那些古老的山水和建筑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场景和风光特色而依存着。故乡的一切都被传统的伦理道德熏陶着,被世代相传的耕读文化浸润着。
老家的兄弟告诉我,那片曾经广种薄收的土地,如今已被改造成4A级景区了。于是,我走进故乡,慢慢地在村中走上一圈,看到年少时爬过的大树、洗澡的清水塘和村头纳凉的晒谷场已离我而去,看到许久无人居住的老屋已渐渐风化,看到许久无人行走的小径已渐渐消痕,听到村里那位很会讲故事的老爷爷和看着我长大给过我关爱的几位大娘已驾鹤西去,一种来自心底的不舍和悲伤油然而生。
在村边那条更加清澈而美丽的小河边,我陆续和邻居、亲友、长辈交流,并很快把“官话”切换成方言,我的心灵渐渐安静下来。小河和乡音,有如植入人脑的一张永久“声”份证,一下子激活了隐藏在大脑中的文化密码,真切地牵出浓浓的乡情和乡愁。这时候,不管是风化的老屋、消痕的小径,还是清波粼粼的小河,都成为我乡愁最好的载体,我的心灵终于满含着乡愁回家了。
我看到更多的,是故乡的变迁。雷鼓山、神通寺、赖公山、上摊堰、凤赖墩、涧峰大田畈、护水双峰、水中央墩已经被村民们改造成涧峰八景。用鹅卵石铺就的村巷,四通八达,像极了迷宫,锁住了这千年古村的神韵。村口的土路变成柏油路,每天都有城里人开着私家车在乡道上逛风景拍视频发朋友圈。五彩缤纷的田野上,水稻田成了采摘园,满园的葡萄、西瓜、草莓和各种时鲜蔬菜,通过“互联网+平台”,走向消费市场的“诗和远方”。村里的农民已经成老板,村姑变导游,连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校,也变成了文化礼堂。更让人震惊的是:这里正全面启动的“乡村国际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开创性地围绕现有乡村空间、产业、人口进行全方位的更新和布局,着力打造从“村落”向“社区”转型的高标准乡村形态、从“低端”向“高端”转型的高质量乡村产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高品位乡村文化、从“单一”向“统筹”转型的高颜值乡村生态、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使之成为中国乡村小康生活“新样板”。
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国际范”,沧桑巨变的故乡,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重要见证,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生动样本。我有幸出生在这样一方土地上,传承着这方土地上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我有幸可以拥有对这片土地的眺望和挂念,这是一个人对于文化母体和人生归属的高度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