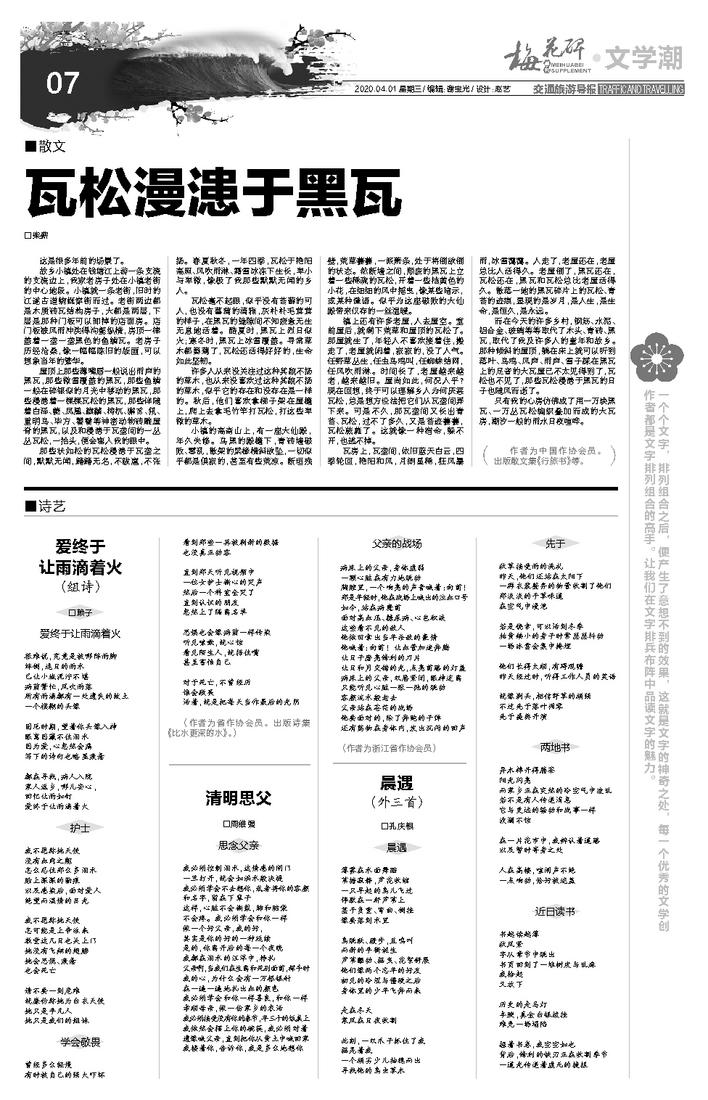这是很多年前的场景了。
故乡小镇处在钱塘江上游一条支流的支流边上,我家老房子处在小镇老街的中心地段。小镇就一条老街,旧时的江遂古道蜿蜒穿街而过。老街两边都是木质砖瓦结构房子,大都是两层,下层是那种门板可以卸掉的店面房。店门板被风雨冲洗得沟壑纵横,房顶一律盖着一垄一垄黑色的鱼鳞瓦。老房子历经沧桑,像一幅幅陈旧的版画,可以想象当年的繁华。
屋顶上那些薄嘴唇一般说出雨声的黑瓦,那些微雪覆盖的黑瓦,那些鱼鳞一般在碎银似的月光中移动的黑瓦,那些漫漶着一棵棵瓦松的黑瓦,那些伴随着白泽、夔、凤凰、麒麟、梼杌、獬豸、犼、重明鸟、毕方、饕餮等神密动物砖雕屋脊的黑瓦,以及和漫漶于瓦垄间的一丛丛瓦松,一抬头,便会窜入我的眼中。
那些状如松的瓦松漫漶于瓦垄之间,默默无闻,籍籍无名,不跋扈,不张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瓦松于艳阳高照、风吹雨淋、霜雪冰冻下生长,卑小与卑微,像极了我那些默默无闻的乡人。
瓦松毫不起眼,似乎没有苔藓的可人,也没有菖蒲的清雅,灰朴朴毛茸茸的样子,在黑瓦的缝隙间不知疲惫无生无息地活着。酷夏时,黑瓦上烈日似火;寒冬时,黑瓦上冰雪覆盖。寻常草木都萎蔫了,瓦松还活得好好的,生命如此坚韧。
许多人从来没关注过这种其貌不扬的草木,也从来没喜欢过这种其貌不扬的草木,似乎它的存在和没存在是一样的。秋后,他们喜欢拿梯子架在屋檐上,爬上去拿毛竹竿打瓦松,打这些卑微的草木。
小镇的高斋山上,有一座大仙殿,年久失修。乌黑的殿檐下,青砖墙破败、零乱,散架的梁椽横斜欲坠,一切似乎都是俱寂的,甚至有些荒凉。断垣残壁,荒草萋萋,一派萧条,处于将倒欲倒的状态。然断墙之间,颓废的黑瓦上立着一些稀疏的瓦松,开着一些桔黄色的小花,在细细的风中摇曳,像某些暗示,或某种谶语。似乎为这座破败的大仙殿带来仅存的一丝温暖。
镇上还有许多老屋,人去屋空。堂前屋后,就剩下荒草和屋顶的瓦松了。那屋就生了,年轻人不喜欢接着住,搬走了,老屋就闲着,寂寂的,没了人气。任野草丛生,任虫鸟鸣叫,任蜘蛛结网,任风吹雨淋。时间长了,老屋越来越老,越来越旧。屋尚如此,何况人乎?现在回想,终于可以理解乡人为何厌恶瓦松,总是想方设法把它们从瓦垄间弄下来。可是不久,那瓦垄间又长出青苔、瓦松,过不了多久,又是苔迹萋萋,瓦松葳蕤了。这就像一种宿命,躲不开,也逃不掉。
瓦房上,瓦垄间,依旧蓝天白云,四季轮回,艳阳和风,月朗星稀,狂风暴雨,冰雪霭霭。人走了,老屋还在,老屋总比人活得久。老屋倒了,黑瓦还在,瓦松还在,黑瓦和瓦松总比老屋活得久。散落一地的黑瓦碎片上的瓦松、青苔的迹痕,显现的是岁月,是人生,是生命,是恒久,是永远。
而在今天的许多乡村,钢筋、水泥、铝合金、玻璃等等取代了木头、青砖、黑瓦,取代了我及许多人的童年和故乡。那种倾斜的屋顶,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落叶、鸟鸣、风声、雨声、雪子踩在黑瓦上的足音的大瓦屋已不太见得到了,瓦松也不见了,那些瓦松漫漶于黑瓦的日子也随风而逝了。
只有我的心房仿佛成了用一万块黑瓦、一万丛瓦松编织叠加而成的大瓦房,潮汐一般的雨水日夜喧哗。
□柴薪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行旅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