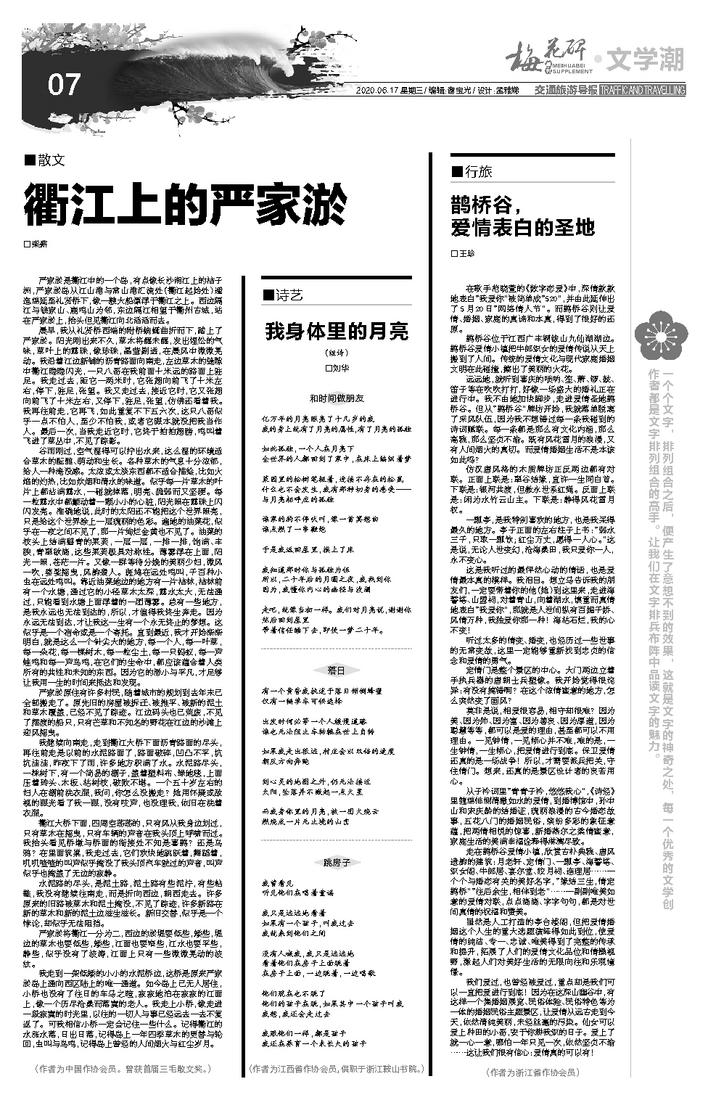严家淤是衢江中的一个岛,有点像长沙湘江上的桔子洲,严家淤岛从江山港与常山港汇流处(衢江起始处)逶迤绵延至礼贤桥下,像一艘大船漂浮于衢江之上。西边隔江与钱家山、鹿鸣山为邻,东边隔江相望于衢州古城,站在严家淤上,抬头但见衢江向北滔滔而去。
晨早,我从礼贤桥西端的附桥蜿蜒曲折而下,踏上了严家淤。阳光刚出来不久,草木将醒未醒,发出惺忪的气味,草叶上的露珠,像珍珠,晶莹剔透,在晨风中微微晃动。我沿着江边新铺的沥青路面向南走,左边草木的缝隙中衢江隐隐闪光,一只八哥在我前面十米远的路面上驻足。我走过去,距它一两米时,它张翅向前飞了十米左右,停下,驻足,张望。我又走过去,接近它时,它又张翅向前飞了十米左右,又停下,驻足,张望,仿佛还看着我。我再往前走,它再飞,如此重复不下五六次,这只八哥似乎一点不怕人,至少不怕我,或者它跟本就没把我当作人。最后一次,当我走近它时,它终于拍拍翅膀,鸣叫着飞进了草丛中,不见了踪影。
谷雨刚过,空气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这么湿的环境适合草木的酝酿、萌动和生长。各种草木的气息十分浓郁,给人一种淹没感。太浓或太淡东西都不适合描绘,比如火焰的灼热,比如炊烟和清水的味道。似乎每一片草木的叶片上都沾满露水,一碰就掉落,明亮、脆弱而又坚硬。每一粒露水中都颤动着一颗小小的心脏,阳光照在露珠上闪闪发亮。准确地说,此时的太阳还不能把这个世界照亮,只是给这个世界涂上一层瑰丽的色彩。遍地的油菜花,似乎在一夜之间不见了,那一片绚烂金黄也不见了。油菜的枝头上结满碧青的果荚,一层一层,一排一排,饱满、丰腴,青翠欲滴,这些果荚极具对称性。薄雾浮在上面,阳光一照,苍茫一片。又像一群等待分娩的美丽少妇,微风一吹,婆娑摇曳,风韵袭人。斑鸠在远处鸣叫,千百种小虫在远处鸣叫。靠近油菜地边的地方有一片桔林,桔林前有一个水塘,通过它的小径草木太深,露水太大,无法通过,只能看到水塘上面浮着的一团薄雾。总有一些地方,是我永远也无法到达的,所以,才值得我终生奔走。因为永远无法到达,才让我这一生有一个永无终止的梦想。这似乎是一个宿命或是一个寄托。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渐渐明白,就是这么一个针尖大的地方,每一个人,每一叶草,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木,每一粒尘土,每一只蚂蚁,每一声蛙鸣和每一声鸟鸣,在它们的生命中,都应该蕴含着人类所有的共性和未知的东西。因为它的渺小与平凡,才足够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来抵达和发现。
严家淤原住有许多村民,随着城市的规划到去年末已全部搬走了。原先旧的房屋被拆迁、被推平、被新的泥土和草木覆盖,已经不见了踪迹。江边码头也已荒废,不见了摆渡的船只,只有芒草和不知名的野花在江边的沙滩上迎风摇曳。
我继续向南走,走到衢江大桥下面沥青路面的尽头,再往前走是以前的水泥路面了,路面破碎,凹凸不平,坑坑洼洼,昨夜下了雨,许多地方积满了水。水泥路尽头,一株树下,有一个简易的棚子,盖着塑料布、绿地毯,上面压着砖头、木板、枯树枝,破败不堪。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在棚前洗衣服,我问,你怎么没搬走?她用怀疑或敌视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也没理我,依旧在洗着衣服。
衢江大桥下面,四周空荡荡的,只有风从我身边划过,只有草木在摇曳,只有车辆的声音在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我抬头看见桥墩与桥面的衔接处不知是喜鹊?还是乌鸦?在里面筑巢,我走过去,它们欢快地跳跃着,舞蹈着,叽叽喳喳的叫声似乎掩没了我头顶汽车驶过的声音,叫声似乎也掩盖了无边的寂静。
水泥路的尽头,是泥土路,泥土路有些泥泞,有些粘鞋,我没有继续往南走,而是折向西边,朝西走去。许多原来的旧路被草木和泥土掩没,不见了踪迹,许多新路在新的草木和新的泥土边滋生滋长。新旧交替,似乎是一个悖论,却似乎无法阻挡。
严家淤将衢江一分为二,西边的淤堤要低些,矮些,堤边的草木也要低些,矮些,江面也要窄些,江水也要平些,静些,似乎没有了波涛,江面上只有一些微微晃动的波纹。
我走到一架低矮的小小的水泥桥边,这桥是原来严家淤岛上通向西区陆上的唯一通道。如今岛上已无人居住,小桥也没有了往日的车马之暄,寂寂地泊在寂寂的江面上,像一个历尽沧桑而落寞的老人。我走上小桥,像走进一段寂寞的时光里,以往的一切人与事已经远去一去不复返了。可我相信小桥一定会记住一些什么。记得衢江的水涨水落,日出日落,记得岛上一年四季草木的更替与轮回,虫叫与鸟鸣,记得岛上曾经的人间烟火与红尘岁月。
□柴薪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