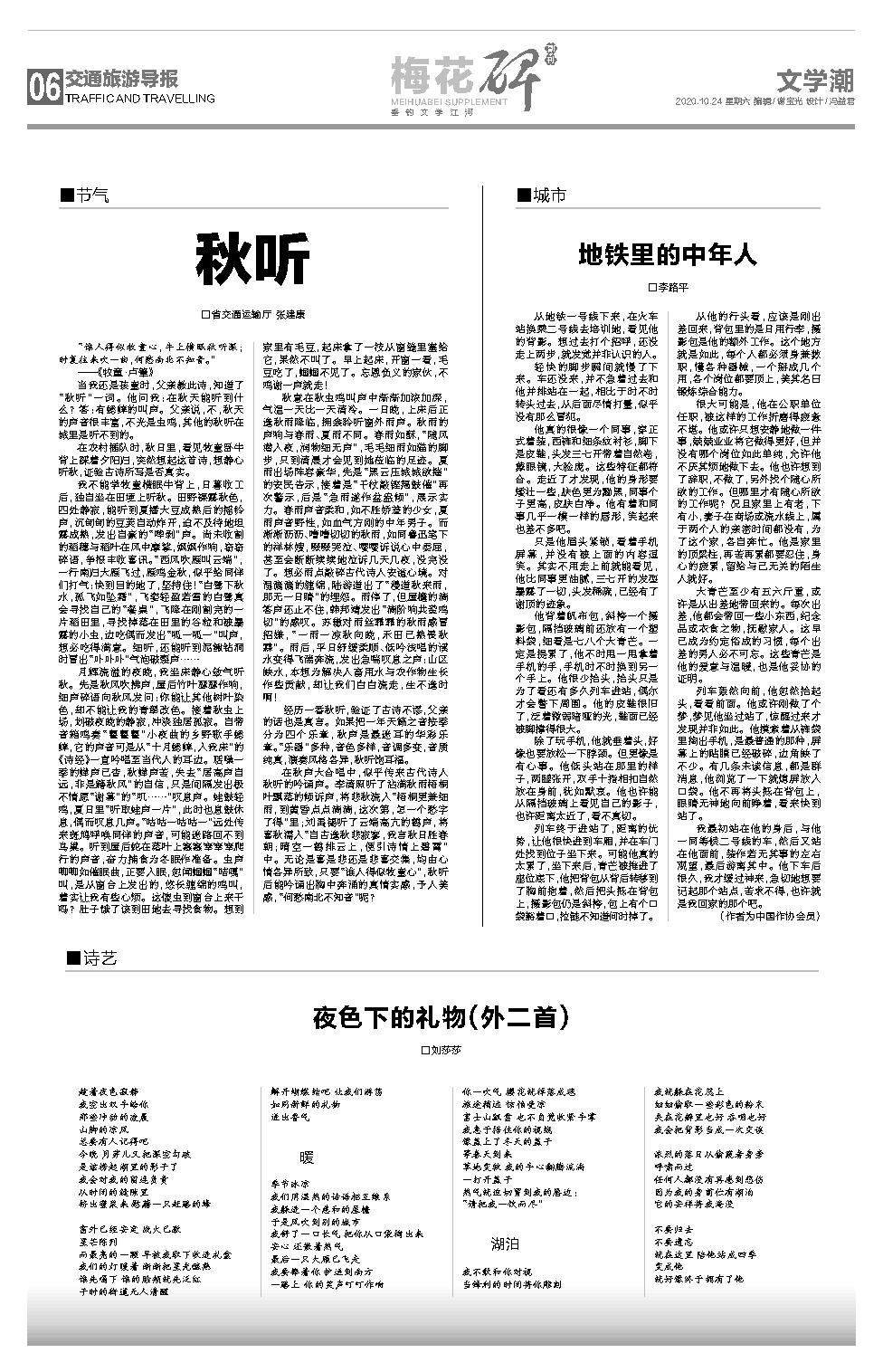□省交通运输厅 张建康
“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
——《牧童·卢肇》
当我还是孩童时,父亲教此诗,知道了“秋听”一词。他问我:在秋天能听到什么?答:有蟋蟀的叫声。父亲说,不,秋天的声音很丰富,不光是虫鸣,其他的秋听在城里是听不到的。
在农村插队时,秋日里,看见牧童卧牛背上踩着夕阳归,突然想起这首诗,想静心听秋,证验古诗所写是否真实。
我不能学牧童横眠牛背上,日暮收工后,独自坐在田埂上听秋。田野裸露秋色,四处静寂,能听到夏播大豆成熟后的摇铃声,沉甸甸的豆荚自动炸开,迫不及待地坦露成熟,发出自豪的“哔剥”声。尚未收割的稻穗与稻叶在风中摩挲,飒飒作响,窃窃碎语,争报丰收喜讯。“西风吹雁叫云端”,一行南归大雁飞过,雁鸣金秋,似乎给同伴们打气:快到目的地了,坚持住!“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飞姿轻盈若雪的白鹭真会寻找自己的“餐桌”,飞降在刚割完的一片稻田里,寻找掉落在田里的谷粒和被暴露的小虫,边吃偶而发出“呱一呱一”叫声,想必吃得满意。细听,还能听到泥鳅钻洞时冒出“卟卟卟”气泡破裂声……
月辉流溢的夜晚,我坐床静心敛气听秋。先是秋风吹拂声,屋后竹叶瑟瑟作响,细声碎语向秋风发问:你能让其他树叶染色,却不能让我的青翠改色。接着秋虫上场,划破夜晚的静寂,冲淡独居孤寂。自带音箱鸣奏“瞿瞿瞿”小夜曲的乡野歌手蟋蟀,它的声音可是从“十月蟋蟀,入我床”的《诗经》一直吟唱至当代人的耳边。聒噪一季的蝉声已杳,秋蝉声苦,失去“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的自信,只是间隔发出极不情愿“谢幕”的“叽……”叹息声。蛙鼓轻鸣,夏日里“听取蛙声一片”,此时也息鼓休息,偶而叹息几声。“咕咕一咕咕一”远处传来斑鸠呼唤同伴的声音,可能迷路回不到鸟巢。听到屋后蛇在落叶上窸窸窣窣窣爬行的声音,奋力捕食为冬眠作准备。虫声唧唧如催眠曲,正要入眠,忽闻蝈蝈“咭嘎”叫,是从窗台上发出的,悠长缠绵的鸣叫,着实让我有些心烦。这傻虫到窗台上来干吗?肚子饿了该到田地去寻找食物。想到家里有毛豆,起床拿了一枝从窗缝里塞给它,果然不叫了。早上起床,开窗一看,毛豆吃了,蝈蝈不见了。忘恩负义的家伙,不鸣谢一声就走!
秋意在秋虫鸣叫声中渐渐加浓加深,气温一天比一天清冷。一日晚,上床后正逢秋雨降临,拥衾聆听窗外雨声。秋雨的声响与春雨、夏雨不同。春雨如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毛毛细雨如猫的脚步,只到清晨才会见到她莅临的足迹。夏雨出场阵容豪华,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安民告示,接着是“千杖敲铿羯鼓催”再次警示,后是“急雨遂作盆盎倾”,展示实力。春雨声音柔和,如不胜娇羞的少女,夏雨声音野性,如血气方刚的中年男子。而淅淅沥沥、嘈嘈切切的秋雨,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啜啜哭泣、嘤嘤诉说心中委屈,甚至会断断续续地泣诉几天几夜,没完没了。想必雨点敲碎古代诗人安谧心境。对湿漉漉的缠绵,陆游道出了“漫道秋来雨,那无一日睛”的埋怨。雨停了,但屋檐的滴答声还止不住,韩邦靖发出“滴阶响共蛩鸣切”的感叹。苏辙对雨丝霏霏的秋雨感冒招嫌,“一雨一凉秋向晚,禾田已熟畏秋霖”。雨后,平日舒缓柔顺、低吟浅唱的溪水变得飞湍奔流,发出急喘叹息之声:山区缺水,本想为解决人畜用水与农作物生长作些贡献,却让我们白白流走,生不逢时啊!
经历一番秋听,验证了古诗不谬,父亲的话也是真言。如果把一年天籁之音按季分为四个乐章,秋声是最迷耳的华彩乐章。“乐器”多种,音色多样,音调多变,音质纯真,演奏风格各异,秋听饱耳福。
在秋声大合唱中,似乎传来古代诗人秋听的吟诵声。李清照听了沾满秋雨梧桐叶飘落的倾诉声,将悲秋流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里;刘禹锡听了云端高亢的鹤声,将喜秋濡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中。无论是喜是悲还是悲喜交集,均由心情各异所致,只要“谁人得似牧童心”,秋听后能吟诵出胸中奔涌的真情实感,予人美感,“何愁南北不知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