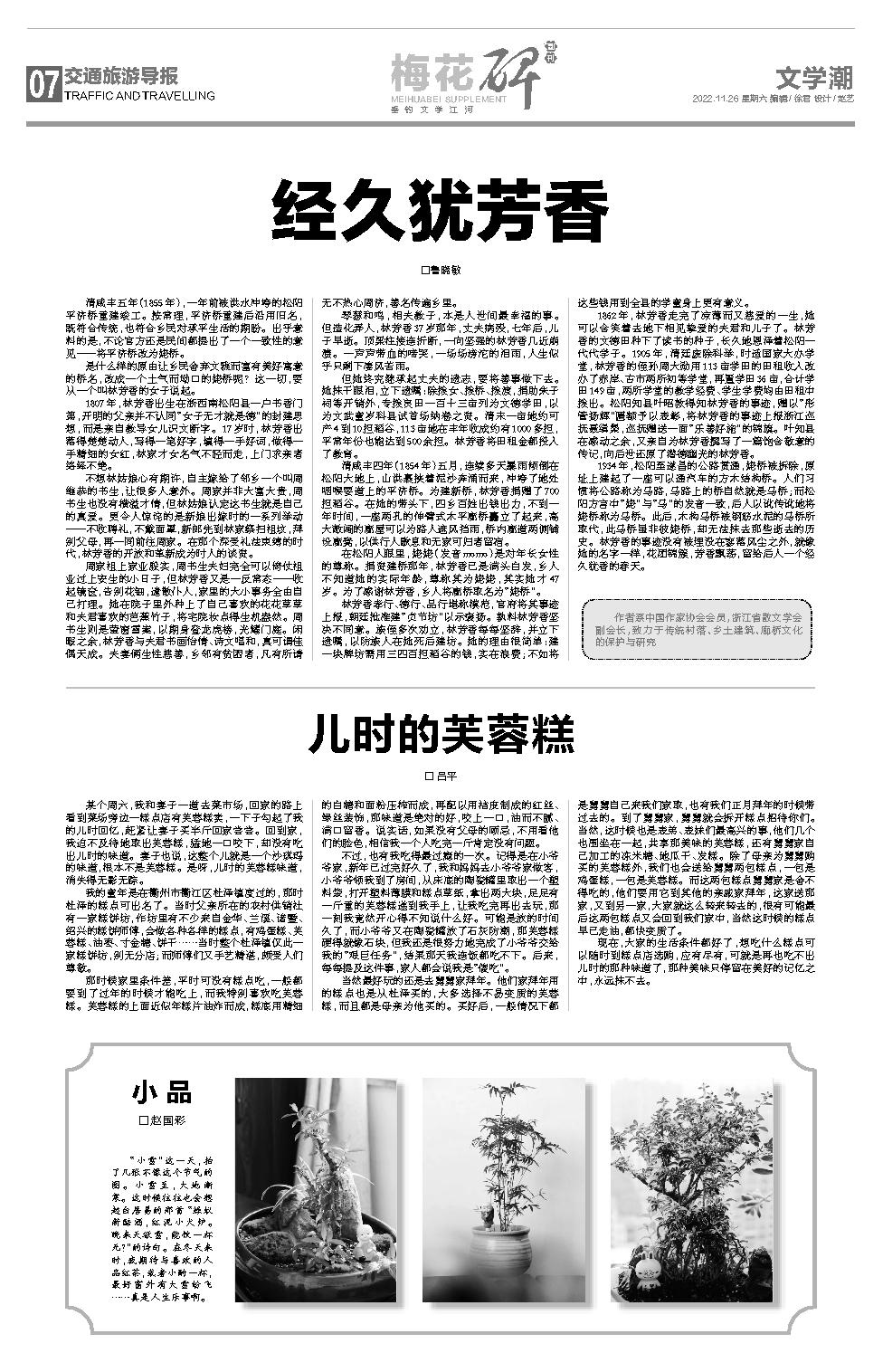清咸丰五年(1855年),一年前被洪水冲垮的松阳平济桥重建竣工。按常理,平济桥重建后沿用旧名,既符合传统,也符合乡民对承平生活的期盼。出乎意料的是,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提出了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将平济桥改为姥桥。
是什么样的原由让乡民舍弃文雅而富有美好寓意的桥名,改成一个土气而坳口的姥桥呢?这一切,要从一个叫林芳香的女子说起。
1807年,林芳香出生在浙西南松阳县一户书香门第,开明的父亲并不认同“女子无才就是德”的封建思想,而是亲自教导女儿识文断字。17岁时,林芳香出落得楚楚动人,写得一笔好字,填得一手好词,做得一手精细的女红,林家才女名气不胫而走,上门求亲者络绎不绝。
不想林姑娘心有期许,自主嫁给了邻乡一个叫周维恭的书生,让很多人意外。周家并非大富大贵,周书生也没有横溢才情,但林姑娘认定这书生就是自己的真爱。更令人惊诧的是新娘出嫁时的一系列举动——不收聘礼,不戴面罩,新郎先到林家祭扫祖坟,拜别父母,再一同前往周家。在那个深受礼法束缚的时代,林芳香的开放和革新成为时人的谈资。
周家祖上家业殷实,周书生夫妇完全可以倚仗祖业过上安生的小日子,但林芳香又是一反常态——收起镜奁,告别花钿,遣散仆人,家里的大小事务全由自己打理。她在院子里外种上了自己喜欢的花花草草和夫君喜欢的芭蕉竹子,将宅院妆点得生机盎然。周书生则是萤窗雪案,以期身登龙虎榜,光耀门庭。闲暇之余,林芳香与夫君书画怡情、诗文唱和,真可谓佳偶天成。夫妻俩生性慈善,乡邻有贫困者,凡有所请无不热心周济,善名传遍乡里。
琴瑟和鸣,相夫教子,本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但造化弄人,林芳香37岁那年,丈夫病殁,七年后,儿子早逝。顶梁柱接连折断,一向坚强的林芳香几近崩溃。一声声带血的啼哭,一场场滂沱的泪雨,人生似乎只剩下凄风苦雨。
但她终究继承起丈夫的遗志,要将善事做下去。她抹干眼泪,立下遗嘱:除拨女、拨桥、拨渡,捐助朱子祠等开销外,专拨良田一百十三亩列为文德学田,以为文武童岁科县试首场纳卷之资。清末一亩地约可产4到10担稻谷,113亩地在丰年收成约有1000多担,平常年份也能达到500余担。林芳香将田租金都投入了教育。
清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连续多天暴雨倾倒在松阳大地上,山洪裹挟着泥沙奔涌而来,冲垮了地处咽喉要道上的平济桥。为建新桥,林芳香捐赠了700担稻谷。在她的带头下,四乡百姓出钱出力,不到一年时间,一座两孔的伸臂式木平廊桥矗立了起来,高大敞阔的廊屋可以为路人遮风挡雨,桥内廊道两侧铺设廊凳,以供行人歇息和无家可归者留宿。
在松阳人眼里,姥姥(发音momo)是对年长女性的尊称。捐资建桥那年,林芳香已是满头白发,乡人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尊称其为姥姥,其实她才47岁。为了感谢林芳香,乡人将廊桥取名为“姥桥”。
林芳香孝行、德行、品行堪称模范,官府将其事迹上报,朝廷批准建“贞节坊”以示褒扬。孰料林芳香坚决不同意。族侄多次劝立,林芳香每每坚辞,并立下遗嘱,以防族人在她死后建坊。她的理由很简单:建一块牌坊需用三四百担稻谷的钱,实在浪费;不如将这些钱用到全县的学童身上更有意义。
1862年,林芳香走完了凉薄而又慈爱的一生,她可以含笑着去地下相见挚爱的夫君和儿子了。林芳香的文德田种下了读书的种子,长久地恩泽着松阳一代代学子。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时适国家大办学堂,林芳香的侄孙周大勋用113亩学田的田租收入改办了赤岸、古市两所初等学堂,再置学田36亩,合计学田149亩,两所学堂的教学经费、学生学费均由田租中拨出。松阳知县叶昭敦得知林芳香的事迹,赠以“彤管扬辉”匾额予以表彰,将林芳香的事迹上报浙江巡抚聂缉椝,巡抚赠送一面“乐善好施”的锦旗。叶知县在感动之余,又亲自为林芳香撰写了一篇饱含敬意的传记,向后世还原了潜德幽光的林芳香。
1934年,松阳至遂昌的公路贯通,姥桥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可以通汽车的方木结构桥。人们习惯将公路称为马路,马路上的桥自然就是马桥;而松阳方言中“姥”与“马”的发音一致,后人以讹传讹地将姥桥称为马桥。此后,木构马桥被钢筋水泥的马桥所取代,此马桥虽非彼姥桥,却无法抹去那些逝去的历史。林芳香的事迹没有被埋没在寥落风尘之外,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花团锦簇,芳香飘荡,留给后人一个经久犹香的春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廊桥文化的保护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