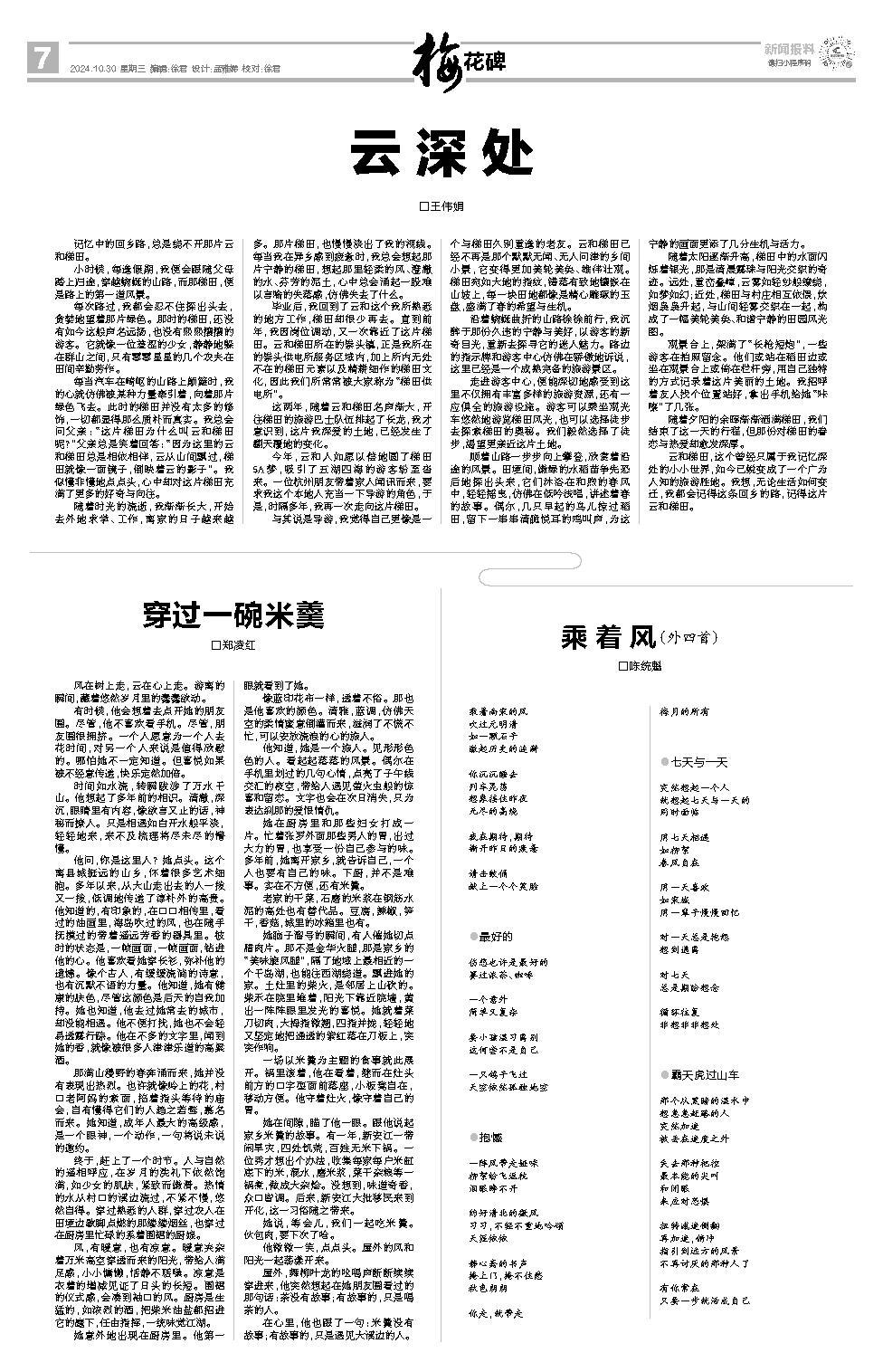风在树上走,云在心上走。游离的瞬间,藏着悠然岁月里的蠢蠢欲动。
有时候,他会想着去点开她的朋友圈。尽管,他不喜欢看手机。尽管,朋友圈很拥挤。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人去花时间,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值得欣慰的。哪怕她不一定知道。但喜悦如果被不经意传递,快乐定然加倍。
时间如水流,转瞬跋涉了万水千山。他想起了多年前的相识。清澈,深沉,眼睛里有内容,像欲言又止的话,神秘而撩人。只是相遇如白开水般平淡,轻轻地来,来不及梳理将尽未尽的懵懂。
他问,你是这里人?她点头。这个离县城挺远的山乡,怀着很多艺术细胞。多年以来,从大山走出去的人一拨又一拨,低调地传递了淳朴外的高贵。他知道的,有印象的,在口口相传里,看过的油画里,海岛吹过的风,也在随手抚摸过的带着遥远芳香的器具里。彼时的状态是,一帧画面,一帧画面,钻进他的心。他喜欢看她穿长衫,弥补他的遗憾。像个古人,有缓缓流淌的诗意,也有沉默不语的力量。他知道,她有健康的肤色,尽管这颜色是后天的自我加持。她也知道,他去过她常去的城市,却没能相遇。他不便打扰,她也不会轻易透露行踪。他在不多的文字里,闻到她的香,就像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高粱酒。
那满山漫野的春奔涌而来,她并没有表现出热烈。也许就像岭上的花,村口老阿妈的索面,掐着指头等待的庙会,自有懂得它们的人趋之若鹜,慕名而来。她知道,成年人最大的高级感,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将说未说的邀约。
终于,赶上了一个时节。人与自然的遥相呼应,在岁月的洗礼下依然饱满,如少女的肌肤,紧致而嫩滑。热情的水从村口的溪边流过,不紧不慢,悠然自得。穿过熟悉的人群,穿过农人在田埂边歇脚点燃的那缕缕烟丝,也穿过在厨房里忙碌的系着围裙的厨娘。
风,有暖意,也有凉意。暖意夹杂着万米高空穿透而来的阳光,带给人满足感,小小慵懒,恬静不聒噪。凉意是衣着的增减见证了日头的长短。围裙的仪式感,会凑到袖口的风。厨房是生猛的,如浓烈的酒,把柴米油盐都招进它的麾下,任由指挥,一统味觉江湖。
她意外地出现在厨房里。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像蓝印花布一样,透着不俗。那也是他喜欢的颜色。清雅,蓝调,仿佛天空的柔情蜜意倒灌而来,滋润了不慌不忙,可以安放流浪的心的旅人。
他知道,她是一个旅人。见形形色色的人。看起起落落的风景。偶尔在手机里划过的几句心情,点亮了子午线交汇的夜空,带给人遇见萤火虫般的惊喜和留恋。文字也会在次日消失,只为表达刹那的爱恨情仇。
她在厨房里和那些妇女打成一片。忙着张罗外面那些男人的胃,出过大力的胃,也享受一份自己参与的味。多年前,她离开家乡,就告诉自己,一个人也要有自己的味。下厨,并不是难事。实在不方便,还有米羹。
老家的干菜,石磨的米浆在钢筋水泥的高处也有替代品。豆腐,辣椒,笋干,香菇,城里的冰箱里也有。
她脑子溜号的瞬间,有人催她切点腊肉片。那不是金华火腿,那是家乡的“美味旋风腿”,隔了地域上最相近的一个千岛湖,也能往西湖绕道。飘进她的家。土灶里的柴火,是邻居上山砍的。柴禾在院里堆着,阳光下靠近院墙,黄出一阵阵眼里发光的喜悦。她就着菜刀切肉,大拇指微翘,四指并拢,轻轻地又坚定地把通透的紫红落在刀板上,突突作响。
一场以米羹为主题的食事就此展开。锅里滚着,他在看着,继而在灶头前方的口字型面前落座,小板凳自在,移动方便。他守着灶火,像守着自己的胃。
她在间隙,瞄了他一眼。跟他说起家乡米羹的故事。有一年,新安江一带闹旱灾,四处饥荒,百姓无米下锅。一位秀才想出个办法,收集每家每户米缸底下的米,混水,磨米浆,菜干杂粮等一锅煮,做成大杂烩。没想到,味道奇香,众口皆调。后来,新安江大批移民来到开化,这一习俗随之带来。
她说,等会儿,我们一起吃米羹。伙包肉,要下次了哈。
他微微一笑,点点头。屋外的风和阳光一起荡漾开来。
屋外,舞柳叶龙的吆喝声断断续续穿进来,他突然想起在她朋友圈看过的那句话:茶没有故事;有故事的,只是喝茶的人。
在心里,他也跟了一句:米羹没有故事;有故事的,只是遇见大溪边的人。
□郑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