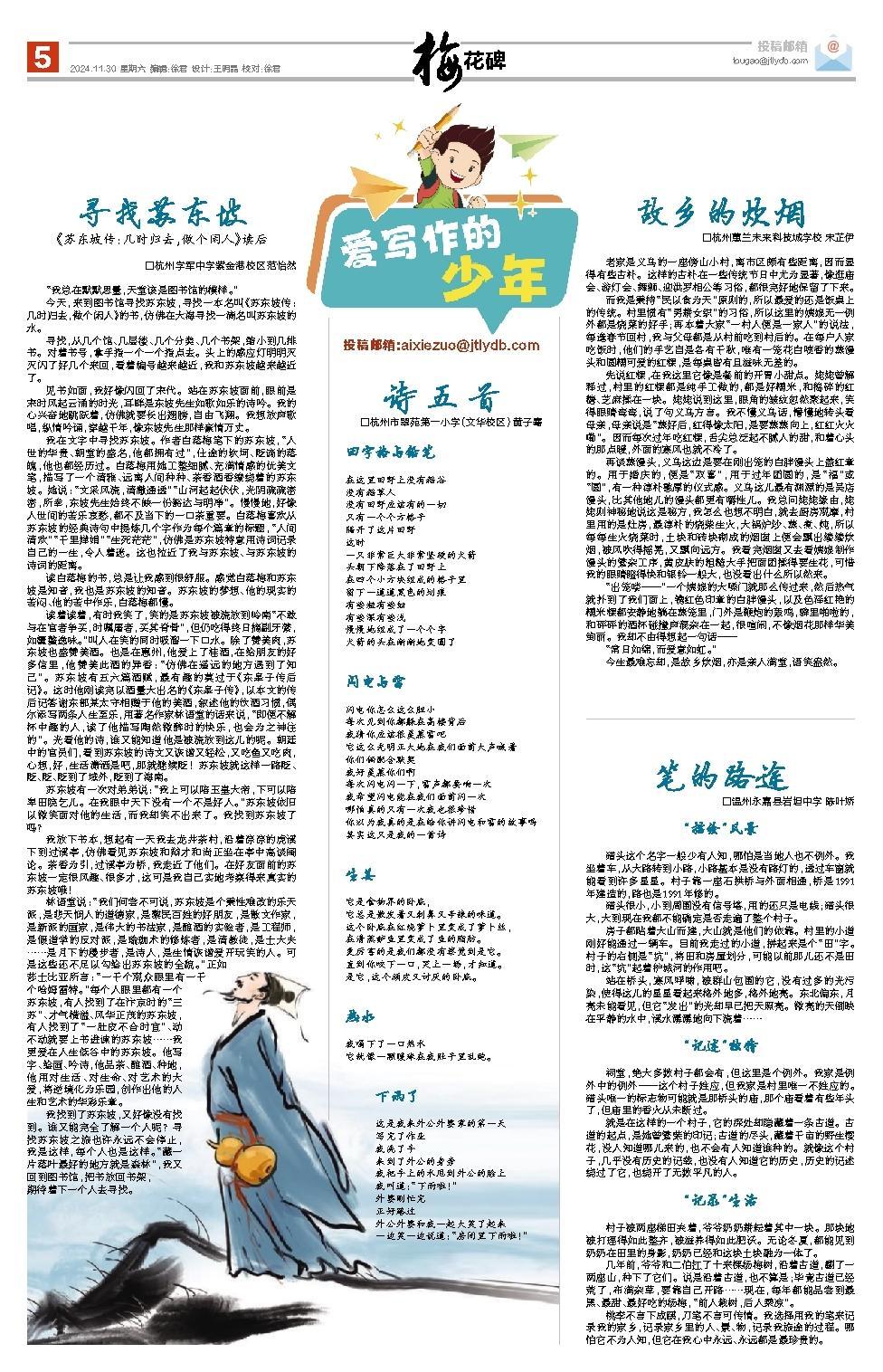老家是义乌的一座傍山小村,离市区颇有些距离,因而显得有些古朴。这样的古朴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尤为显著,像逛庙会、游灯会、舞狮、迎洪罗相公等习俗,都很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而我是秉持“民以食为天”原则的,所以最爱的还是饭桌上的传统。村里惯有“男耕女织”的习俗,所以这里的姨娘无一例外都是烧菜的好手;再本着大家“一村人便是一家人”的说法,每逢春节回村,我与父母都是从村前吃到村后的。在每户人家吃饭时,他们的手艺自是各有千秋,唯有一笼花白喷香的蒸馒头和圆糯可爱的红粿,是每桌皆有且滋味无差的。
先说红粿,在我这里它像是餐前的开胃小甜点。姥姥曾解释过,村里的红粿都是纯手工做的,都是好糯米,和捣碎的红糖、芝麻揉在一块。姥姥说到这里,眼角的皱纹忽然聚起来,笑得眼睛弯弯,说了句义乌方言。我不懂义乌话,懵懂地转头看母亲,母亲说是“蒸好后,红得像太阳,是要蒸蒸向上,红红火火嘞”。因而每次过年吃红粿,舌尖总泛起不腻人的甜,和着心头的那点暖,外面的寒风也就不冷了。
再谈蒸馒头,义乌这边是要在刚出笼的白胖馒头上盖红章的。用于婚庆的,便是“双喜”,用于过年团圆的,是“福”或“圆”,有一种淳朴憨厚的仪式感。义乌这儿最有渊源的是吴店馒头,比其他地儿的馒头都更有嚼性儿。我总问姥姥缘由,姥姥则神秘地说这是秘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去厨房观摩,村里用的是灶房,最淳朴的烧柴生火,大锅炉炒、蒸、煮、炖,所以每每生火烧菜时,土块和砖块砌成的烟囱上便会飘出缕缕炊烟,被风吹得摇晃,又飘向远方。我看完烟囱又去看姨娘制作馒头的繁杂工序,黄皮肤的粗糙大手把面团揉得要生花,可惜我的眼睛瞪得快和银铃一般大,也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
“出笼喽——”一个姨娘的大嗓门就那么传过来,然后热气就扑到了我们面上,镌红色印章的白胖馒头,以及色泽红艳的糯米粿都安静地躺在蒸笼里,门外是鞭炮的轰鸣,噼里啪啦的,和砰砰的酒杯碰撞声混杂在一起,很喧闹,不像烟花那样华美绚丽。我却不由得想起一句话——
“常日如绵,而爱意如虹。”
今生最难忘却,是故乡炊烟,亦是亲人满堂,语笑盎然。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宋芷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