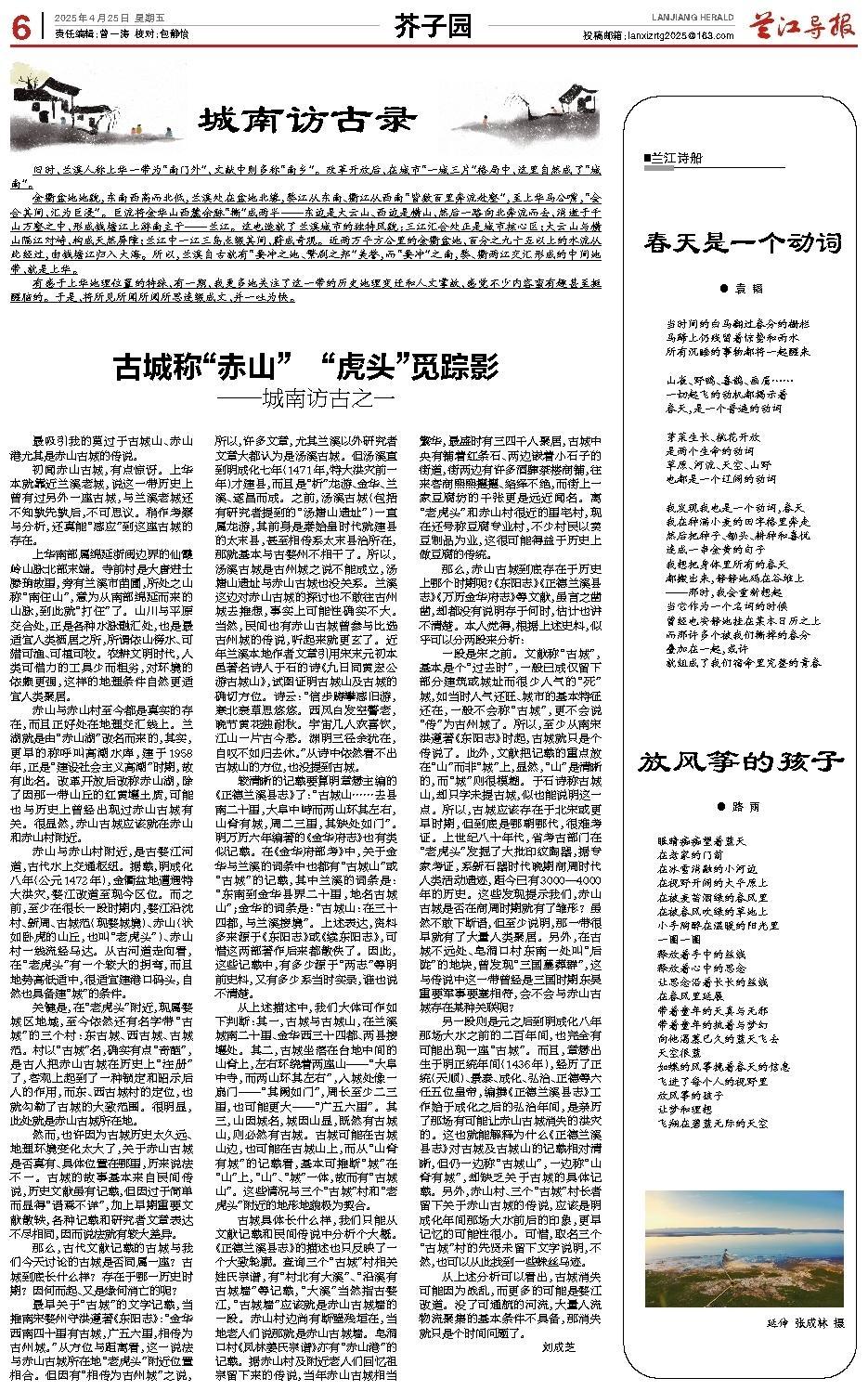城南访古录
旧时,兰溪人称上华一带为“南门外”,文献中则多称“南乡”。改革开放后,在城市“一城三片”格局中,这里自然成了“城南”。
金衢盆地地貌,东南西高而北低,兰溪处在盆地北缘,婺江从东南、衢江从西南“皆数百里奔流赴壑”,至上华马公嘴,“会合其间,汇为巨浸”。巨流将金华山西麓余脉“撕”成两半——东边是大云山、西边是横山,然后一路向北奔流而去,消逝于千山万壑之中,形成钱塘江上游南主干——兰江。这也造就了兰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三江汇合处正是城市核心区;大云山与横山隔江对峙,构成天然屏障;兰江中一江三岛点缀其间,蔚成奇观。近两万平方公里的金衢盆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水流从此经过,由钱塘江归入大海。所以,兰溪自古就有“要冲之地、繁剧之邦”美誉,而“要冲”之南,婺、衢两江交汇形成的中间地带,就是上华。
有感于上华地理位置的特殊,有一期,我更多地关注了这一带的历史地理变迁和人文掌故,感觉不少内容蛮有趣甚至挺醒脑的。于是,将所见所闻所阅所思连缀成文,并一吐为快。
古城称“赤山” “虎头”觅踪影
——城南访古之一
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古城山、赤山港尤其是赤山古城的传说。
初闻赤山古城,有点惊讶。上华本就靠近兰溪老城,说这一带历史上曾有过另外一座古城,与兰溪老城还不知孰先孰后,不可思议。稍作考察与分析,还真能“感应”到这座古城的存在。
上华南部属绵延浙闽边界的仙霞岭山脉北部末端。寺前村是大唐进士滕珦故里,旁有兰溪市苗圃,所处之山称“南住山”,意为从南部绵延而来的山脉,到此就“打住”了。山川与平原交合处,正是各种水脉融汇处,也是最适宜人类栖居之所,所谓依山傍水、可猎可渔、可植可牧。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可借力的工具少而粗劣,对环境的依赖更强,这样的地理条件自然更适宜人类聚居。
赤山与赤山村至今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正好处在地理交汇线上。兰湖就是由“赤山湖”改名而来的,其实,更早的称呼叫高潮水库,建于1958年,正是“建设社会主义高潮”时期,故有此名。改革开放后改称赤山湖,除了因那一带山丘的红黄壤土质,可能也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赤山古城有关。很显然,赤山古城应该就在赤山和赤山村附近。
赤山与赤山村附近,是古婺江河道,古代水上交通枢纽。据载,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金衢盆地遭遇特大洪灾,婺江改道至现今区位。而之前,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婺江沿沈村、新周、古城范(现婺城境)、赤山(状如卧虎的山丘,也叫“老虎头”)、赤山村一线流经马达。从古河道走向看,在“老虎头”有一个较大的拐弯,而且地势高低适中,很适宜建港口码头,自然也具备建“城”的条件。
关键是,在“老虎头”附近,现属婺城区地域,至今依然还有名字带“古城”的三个村:东古城、西古城、古城范。村以“古城”名,确实有点“奇葩”,是古人把赤山古城在历史上“注册”了,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锁定和昭示后人的作用,而东、西古城村的定位,也就勾勒了古城的大致范围。很明显,此处就是赤山古城所在地。
然而,也许因为古城历史太久远、地理环境变化太大了,关于赤山古城是否真有、具体位置在哪里,历来说法不一。古城的故事基本来自民间传说,历史文献虽有记载,但因过于简单而显得“语焉不详”,加上早期重要文献散轶,各种记载和研究者文章表达不尽相同,因而说法就有较大差异。
那么,古代文献记载的古城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古城是否同属一座?古城到底长什么样?存在于哪一历史时期?因何而起、又是缘何消亡的呢?
最早关于“古城”的文字记载,当推南宋婺州守洪遵著《东阳志》:“金华西南四十里有古城,广五六里,相传为古州城。”从方位与距离看,这一说法与赤山古城所在地“老虎头”附近位置相合。但因有“相传为古州城”之说,所以,许多文章,尤其兰溪以外研究者文章大都认为是汤溪古城。但汤溪直到明成化七年(1471年,特大洪灾前一年)才建县,而且是“析”龙游、金华、兰溪、遂昌而成。之前,汤溪古城(包括有研究者提到的“汤塘山遗址”)一直属龙游,其前身是秦始皇时代就建县的太末县,甚至相传系太末县治所在,那就基本与古婺州不相干了。所以,汤溪古城是古州城之说不能成立,汤塘山遗址与赤山古城也没关系。兰溪这边对赤山古城的探讨也不敢往古州城去推想,事实上可能性确实不大。当然,民间也有赤山古城曾参与比选古州城的传说,听起来就更玄了。近年兰溪本地作者文章引用宋末元初本邑著名诗人于石的诗《九日同黄宏公游古城山》,试图证明古城山及古城的确切方位。诗云:“信步踌攀感旧游,寒北衰草思悠悠。西风白发空警老,晚节黄花独耐秋。宇宙几人欢喜饮,江山一片古今愁。渊明三径余犹在,自叹不如归去休。”从诗中依然看不出古城山的方位,也没提到古城。
较清晰的记载要算明章懋主编的《正德兰溪县志》了:“古城山……去县南二十里,大阜中峙而两山环其左右,山脊有城,周二三里,其缺处如门”。明万历六年编著的《金华府志》也有类似记载。在《金华府部考》中,关于金华与兰溪的词条中也都有“古城山”或“古城”的记载,其中兰溪的词条是:“东南到金华县界二十里,地名古城山”;金华的词条是:“古城山:在三十四都,与兰溪接境”。上述表达,资料多来源于《东阳志》或《续东阳志》,可惜这两部著作后来都散佚了。因此,这些记载中,有多少源于“两志”等明前史料,又有多少系当时实录,谁也说不清楚。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大体可作如下判断:其一,古城与古城山,在兰溪城南二十里、金华西三十四都、两县接壤处。其二,古城坐落在台地中间的山脊上,左右环绕着两座山——“大阜中寺,而两山环其左右”,入城处像一扇门——“其阙如门”,周长至少二三里,也可能更大——“广五六里”。其三,山因城名,城因山显,既然有古城山,则必然有古城。古城可能在古城山边,也可能在古城山上,而从“山脊有城”的记载看,基本可推断“城”在“山”上,“山”、“城”一体,故而有“古城山”。这些情况与三个“古城”村和“老虎头”附近的地形地貌极为契合。
古城具体长什么样,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分析个大概。《正德兰溪县志》的描述也只反映了一个大致轮廓。查询三个“古城”村相关姓氏宗谱,有“村北有大溪”、“沿溪有古城墙”等记载,“大溪”当然指古婺江,“古城墙”应该就是赤山古城墙的一段。赤山村边尚有断壁残垣在,当地老人们说那就是赤山古城墙。皂洞口村《凤林姜氏宗谱》亦有“赤山港”的记载。据赤山村及附近老人们回忆祖宗留下来的传说,当年赤山古城相当繁华,最盛时有三四千人聚居,古城中央有铺着红条石、两边嵌着小石子的街道,街两边有许多酒肆茶楼商铺,往来客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而街上一家豆腐坊的千张更是远近闻名。离“老虎头”和赤山村很近的里宅村,现在还号称豆腐专业村,不少村民以卖豆制品为业,这很可能得益于历史上做豆腐的传统。
那么,赤山古城到底存在于历史上哪个时期呢?《东阳志》《正德兰溪县志》《万历金华府志》等文献,虽言之凿凿,却都没有说明存于何时,估计也讲不清楚。本人觉得,根据上述史料,似乎可以分两段来分析:
一段是宋之前。文献称“古城”,基本是个“过去时”,一般已成仅留下部分建筑或城址而很少人气的“死”城,如当时人气还旺、城市的基本特征还在,一般不会称“古城”,更不会说“传”为古州城了。所以,至少从南宋洪遵著《东阳志》时起,古城就只是个传说了。此外,文献把记载的重点放在“山”而非“城”上,显然,“山”是清晰的,而“城”则很模糊。于石诗称古城山,却只字未提古城,似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古城应该存在于北宋或更早时期,但到底是哪朝哪代,很难考证。上世纪八十年代,省考古部门在“老虎头”发掘了大批印纹陶器,据专家考证,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距今已有3000—4000年的历史。这些发现提示我们,赤山古城是否在商周时期就有了雏形?虽然不敢下断语,但至少说明,那一带很早就有了大量人类聚居。另外,在古城不远处、皂洞口村东南一处叫“后陇”的地块,曾发现“三国墓葬群”,这与传说中这一带曾经是三国时期东吴重要军事要塞相符,会不会与赤山古城存在某种关联呢?
另一段则是元之后到明成化八年那场大水之前的二百年间,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一座“古城”。而且,章懋出生于明正统年间(1436年),经历了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正德等六任五位皇帝,编撰《正德兰溪县志》工作始于成化之后的弘治年间,是亲历了那场有可能让赤山古城消失的洪灾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正德兰溪县志》对古城及古城山的记载相对清晰,但仍一边称“古城山”,一边称“山脊有城”,却缺乏关于古城的具体记载。另外,赤山村、三个“古城”村长者留下关于赤山古城的传说,应该是明成化年间那场大水前后的印象,更早记忆的可能性很小。可惜,取名三个“古城”村的先贤未留下文字说明,不然,也可以从此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古城消失可能因为战乱,而更多的可能是婺江改道。没了可通航的河流,大量人流物流聚集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那消失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刘成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