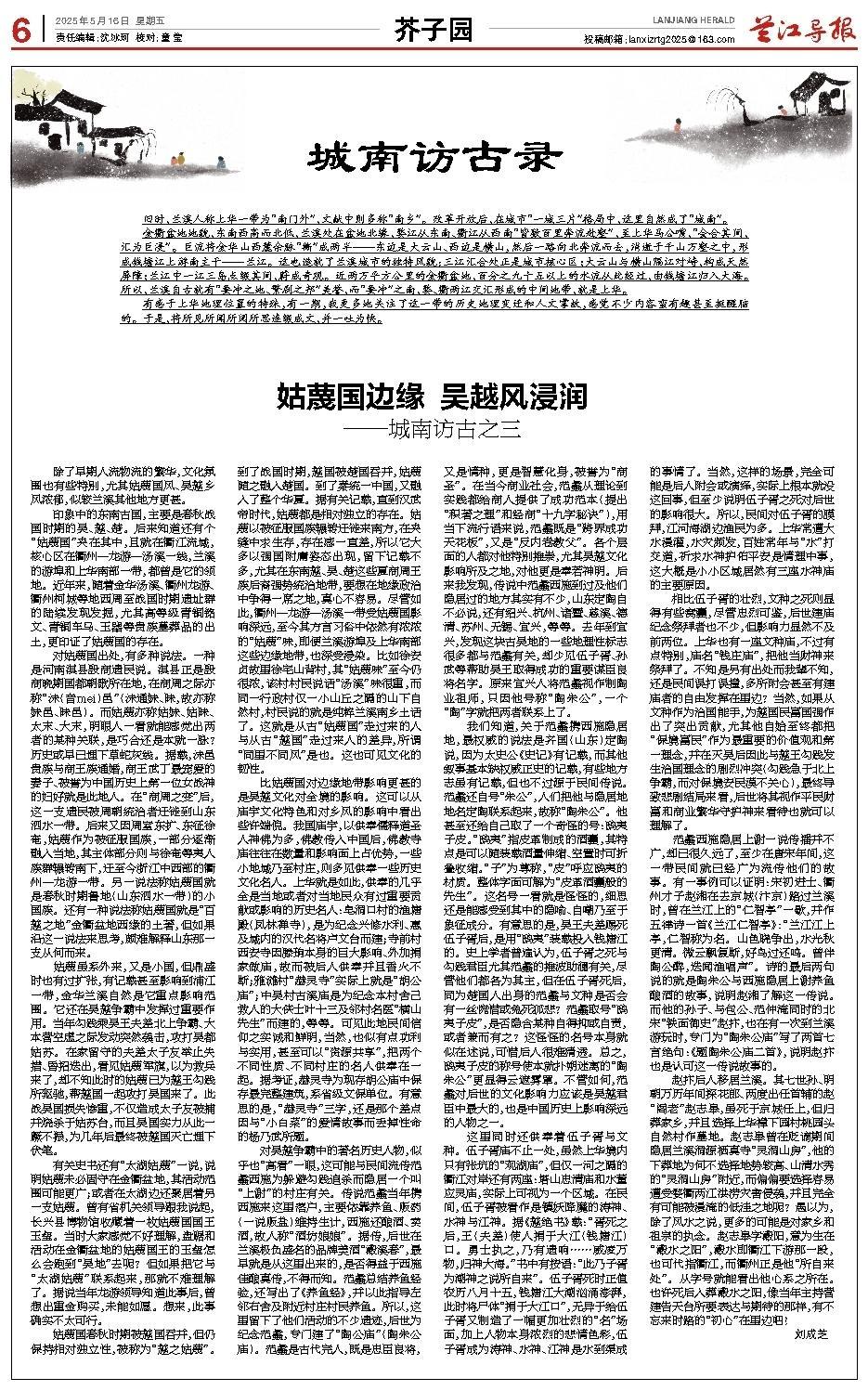姑蔑国边缘 吴越风浸润
——城南访古之三
除了早期人流物流的繁华,文化氛围也有些特别,尤其姑蔑国风、吴越乡风浓郁,似较兰溪其他地方更甚。 印象中的东南古国,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楚。后来知道还有个“姑蔑国”夹在其中,且就在衢江流域,核心区在衢州—龙游—汤溪一线,兰溪的游埠和上华南部一带,都曾是它的领地。近年来,随着金华汤溪、衢州龙游、衢州柯城等地西周至战国时期遗址群的陆续发现发掘,尤其高等级青铜铭文、青铜车马、玉器等贵族墓葬品的出土,更印证了姑蔑国的存在。 对姑蔑国出处,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河南淇县殷商遗民说。淇县正是殷商晚期国都朝歌所在地,在商周之际亦称“沬(音mei)邑”(沬通妹、昧,故亦称妹邑、昧邑)。而姑蔑亦称姑妹、姑昧、太末、大末,明眼人一看就能感觉出两者的某种关联,是巧合还是本就一脉?历史或早已埋下草蛇灰线。据载,沬邑贵族与商王族通婚,商王武丁最宠爱的妻子、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战神的妇好就是此地人。在“商周之变”后,这一支遗民被周朝统治者迁徙到山东泗水一带。后来又因周室东扩、东征徐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逐渐融入当地,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迁至今浙江中西部的衢州—龙游一带。另一说法称姑蔑国就是春秋时期鲁地(山东泗水一带)的小国族。还有一种说法称姑蔑国就是“百越之地”金衢盆地西缘的土著,但如果沿这一说法来思考,颇难解释山东那一支从何而来。 姑蔑虽系外来,又是小国,但鼎盛时也有过扩张,有记载甚至影响到浦江一带,金华兰溪自然是它重点影响范围。它还在吴越争霸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勾践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大本营空虚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攻打吴都姑苏。在家留守的夫差太子友举止失措、昏招迭出,看见姑蔑军旗,以为救兵来了,却不知此时的姑蔑已为越王勾践所驱驰,帮越国一起攻打吴国来了。此战吴国损失惨重,不仅造成太子友被捕并烧杀于姑苏台,而且吴国实力从此一蹶不振,为几年后最终被越国灭亡埋下伏笔。 有关史书还有“太湖姑蔑”一说,说明姑蔑未必固守在金衢盆地,其活动范围可能更广;或者在太湖边还聚居着另一支姑蔑。曾有省机关领导跟我说起,长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枚姑蔑国国王玉玺。当时大家感觉不好理解,盘踞和活动在金衢盆地的姑蔑国王的玉玺怎么会跑到“吴地”去呢?但如果把它与“太湖姑蔑”联系起来,那就不难理解了。据说当年龙游领导知道此事后,曾想出重金购买,未能如愿。想来,此事确实不太可行。 姑蔑国春秋时期被越国吞并,但仍保持相对独立性,被称为“越之姑蔑”。到了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吞并,姑蔑随之融入楚国。到了秦统一中国,又融入了整个华夏。据有关记载,直到汉武帝时代,姑蔑都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姑蔑以被征服国族辗转迁徙来南方,在夹缝中求生存,存在感一直差,所以它大多以强国附庸姿态出现,留下记载不多,尤其在东南越、吴、楚这些夏商周王族后裔强势统治地带,要想在地缘政治中争得一席之地,真心不容易。尽管如此,衢州—龙游—汤溪一带受姑蔑国影响深远,至今其方言习俗中依然有浓浓的“姑蔑”味,即便兰溪游埠及上华南部这些边缘地带,也深受浸染。比如徐安贞故里徐宅山背村,其“姑蔑味”至今仍很浓,该村村民说话“汤溪”味很重,而同一行政村仅一小山丘之隔的山下自然村,村民说的就是纯粹兰溪南乡土话了。这就是从古“姑蔑国”走过来的人与从古“越国”走过来人的差异,所谓“同里不同风”是也。这也可见文化的韧性。 比姑蔑国对边缘地带影响更甚的是吴越文化对全境的影响。这可以从庙宇文化特色和对乡风的影响中看出些许端倪。我国庙宇,以供奉儒释道圣人神佛为多,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寺庙往往在数量和影响面上占优势,一些小地域乃至村庄,则多见供奉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上华就是如此,供奉的几乎全是当地或者对当地民众有过重要贡献或影响的历史名人:皂洞口村的渔塘殿(凤林禅寺),是为纪念兴修水利、惠及域内的汉代名将卢文台而建;寺前村西安寺因滕珦本身的巨大影响、外加捐家做庙,故而被后人供奉并且香火不断;雅滩村“赫灵寺”实际上就是“胡公庙”;中吴村古溪庙是为纪念本村舍己救人的大侠士叶十三及邻村名医“横山先生”而建的,等等。可见此地民间信仰之实诚和鲜明,当然,也似有点功利与实用,甚至可以“资源共享”,把两个不同性质、不同村庄的名人供奉在一起。据考证,赫灵寺为现存胡公庙中保存最完整建筑,系省级文保单位。有意思的是,“赫灵寺”三字,还是那个差点因与“小白菜”的爱情故事而丢掉性命的杨乃武所题。 对吴越争霸中的著名历史人物,似乎也“高看”一眼,这可能与民间流传范蠡西施为躲避勾践追杀而隐居一个叫“上谢”的村庄有关。传说范蠡当年携西施来这里落户,主要依靠养鱼、贩药(一说贩盐)维持生计,西施还酿酒、卖酒,故人称“酒坊娘娘”。据传,后世在兰溪极负盛名的品牌美酒“瀔溪春”,最早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是否得益于西施佳酿真传,不得而知。范蠡总结养鱼经验,还写出了《养鱼经》,并以此指导左邻右舍及附近村庄村民养鱼。所以,这里留下了他们活动的不少遗迹,后世为纪念范蠡,专门建了“陶公庙”(陶朱公庙)。范蠡是古代完人,既是忠臣良将,又是情种,更是智慧化身,被誉为“商圣”。在当今商业社会,范蠡从理论到实践都给商人提供了成功范本(提出“积著之理”和经商“十九字秘诀”),用当下流行语来说,范蠡既是“跨界成功天花板”,又是“反内卷教父”。各个层面的人都对他特别推崇,尤其吴越文化影响所及之地,对他更是奉若神明。后来我发现,传说中范蠡西施到过及他们隐居过的地方其实有不少,山东定陶自不必说,还有绍兴、杭州、诸暨、慈溪、德清、苏州、无锡、宜兴,等等。去年到宜兴,发现这块古吴地的一些地理性标志很多都与范蠡有关,却少见伍子胥、孙武等帮助吴王取得成功的重要谋臣良将名字。原来宜兴人将范蠡视作制陶业祖师,只因他号称“陶朱公”,一个“陶”字就把两者联系上了。 我们知道,关于范蠡携西施隐居地,最权威的说法是齐国(山东)定陶说,因为太史公《史记》有记载,而其他叙事基本缺权威正史的记载,有些地方志虽有记载,但也不过源于民间传说。范蠡还自号“朱公”,人们把他与隐居地地名定陶联系起来,故称“陶朱公”。他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奇怪的号:鸱夷子皮。“鸱夷”指皮革制成的酒囊,其特点是可以随装载酒量伸缩、空置时可折叠收缩。“子”为尊称,“皮”呼应鸱夷的材质。整体字面可解为“皮革酒囊般的先生”。这名号一看就是怪怪的,细思还是能感受到其中的隐喻、自嘲乃至于象征成分。有意思的是,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后,是用“鸱夷”装载投入钱塘江的。史上学者普遍认为,伍子胥之死与勾践君臣尤其范蠡的推波助澜有关,尽管他们都各为其主,但在伍子胥死后,同为楚国人出身的范蠡与文种是否会有一丝惋惜或兔死狐悲?范蠡取号“鸱夷子皮”,是否隐含某种自得抑或自责,或者兼而有之?这怪怪的名号本身就似在述说,可惜后人很难猜透。总之,鸱夷子皮的称号使本就扑朔迷离的“陶朱公”更显得云遮雾罩。不管如何,范蠡对后世的文化影响力应该是吴越君臣中最大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这里同时还供奉着伍子胥与文种。伍子胥庙不止一处,虽然上华境内只有张坑的“观湖庙”,但仅一河之隔的衢江对岸还有两座:塔山忠清庙和水董应灵庙,实际上可视为一个区域。在民间,伍子胥被看作是镇妖降魔的涛神、水神与江神。据《越绝书》载:“胥死之后,王(夫差)使人捐于大江(钱塘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书中有按语:“此乃子胥为潮神之说所自来”。伍子胥死时正值农历八月十五,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此时将尸体“捐于大江口”,无异于给伍子胥又制造了一幅更加壮烈的“名”场面,加上人物本身浓烈的悲情色彩,伍子胥成为涛神、水神、江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当然,这样的场景,完全可能是后人附会或演绎,实际上根本就没这回事,但至少说明伍子胥之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以,民间对伍子胥的膜拜,江河海湖边渔民为多。上华常遭大水漫灌,水灾频发,百姓常年与“水”打交道,祈求水神护佑平安是情理中事,这大概是小小区域居然有三座水神庙的主要原因。 相比伍子胥的壮烈,文种之死则显得有些窝囊,尽管忠烈可鉴,后世建庙纪念祭拜者也不少,但影响力显然不及前两位。上华也有一座文种庙,不过有点特别,庙名“钱庄庙”,把他当财神来祭拜了。不知是另有出处而我辈不知,还是民间误打误撞,多所附会甚至有建庙者的自由发挥在里边?当然,如果从文种作为治国能手,为越国民富国强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他自始至终都把“保境富民”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和第一理念,并在灭吴后因此与越王勾践发生治国理念的剧烈冲突(勾践急于北上争霸,而对保境安民漠不关心),最终导致悲剧结局来看,后世将其视作平民财富和商业繁华守护神来看待也就可以理解了。 范蠡西施隐居上谢一说传播并不广,却已很久远了,至少在唐宋年间,这一带民间就已经广为流传他们的故事。有一事例可以证明:宋初进士、衢州才子赵湘在去京城(汴京)路过兰溪时,曾在兰江上的“仁智亭”一歇,并作五律诗一首《兰江仁智亭》:“兰江江上亭,仁智称为名。山色晓争出,水光秋更清。微云飘复断,好鸟过还鸣。曾伴陶公醉,迭闻渔唱声”。诗的最后两句说的就是陶朱公与西施隐居上谢养鱼酿酒的故事,说明赵湘了解这一传说。而他的孙子、与包公、范仲淹同时的北宋“铁面御史”赵抃,也在有一次到兰溪游玩时,专门为“陶朱公庙”写了两首七言绝句:《题陶朱公庙二首》,说明赵抃也是认可这一传说故事的。 赵抃后人移居兰溪。其七世孙、明朝万历年间探花郎、两度出任首辅的赵“阁老”赵志皋,虽死于京城任上,但归葬家乡,并且选择上华樟下园村桃园头自然村作墓地。赵志皋曾在贬谪期间隐居兰溪洞源栖真寺“灵洞山房”,他的下葬地为何不选择地势较高、山清水秀的“灵洞山房”附近,而偏偏要选择容易遭受婺衢两江洪涝灾害侵袭,并且完全有可能被漫淹的低洼之地呢?愚以为,除了风水之说,更多的可能是对家乡和祖宗的执念。赵志皋字瀔阳,意为生在“瀔水之阳”,瀔水即衢江下游那一段,也可代指衢江,而衢州正是他“所自来处”。从字号就能看出他心系之所在。也许死后入葬瀔水之阳,像当年主持营建告天台所要表达与期待的那样,有不忘来时路的“初心”在里边吧!
刘成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