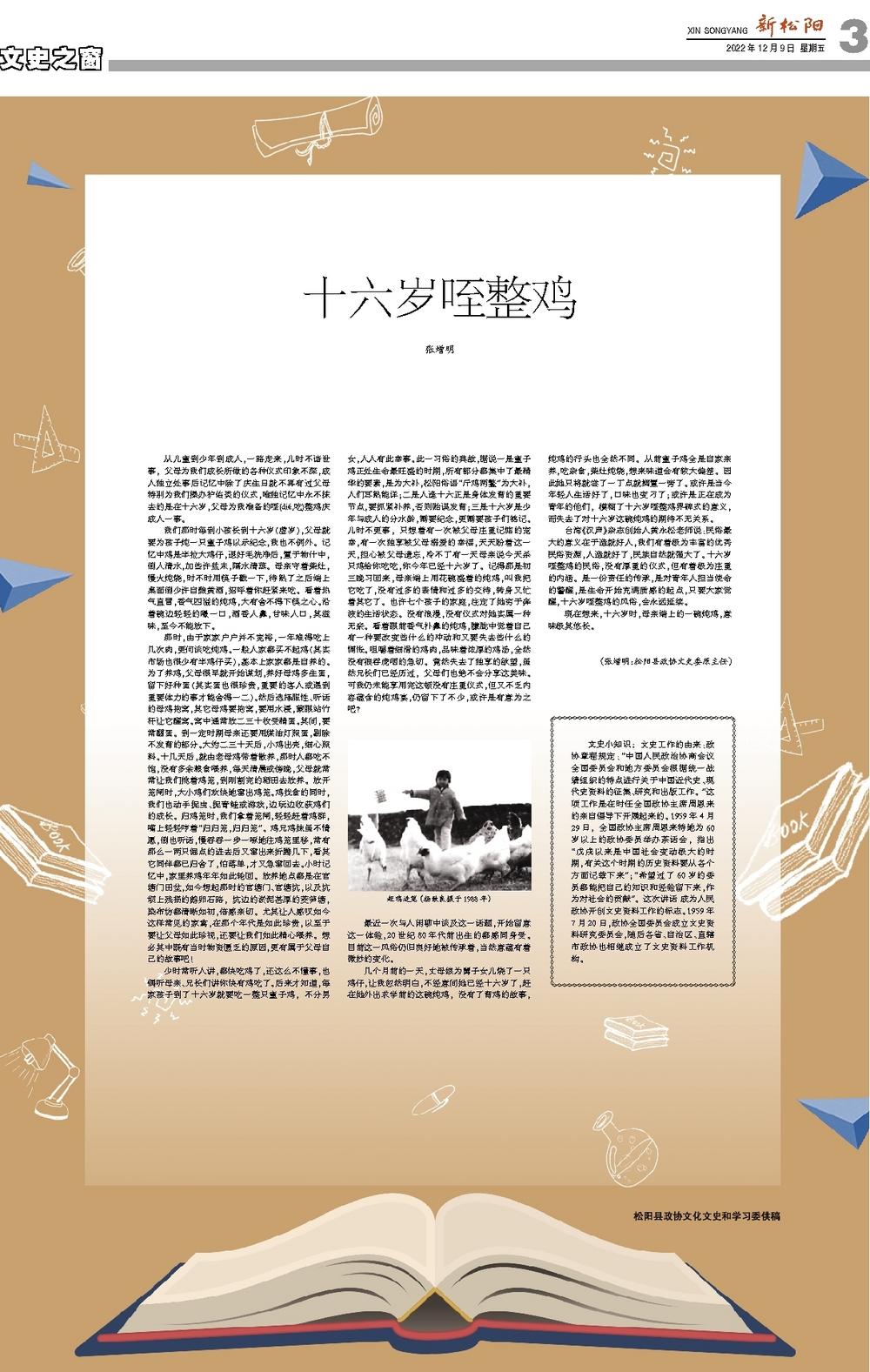从儿童到少年到成人,一路走来,儿时不谙世事,父母为我们成长所做的各种仪式印象不深,成人独立处事后记忆中除了庆生日就不再有过父母特别为我们操办护佑类的仪式,唯独记忆中永不抹去的是在十六岁,父母为我准备的咥(dié,吃)整鸡庆成人一事。
我们那时每到小孩长到十六岁(虚岁),父母就要为孩子炖一只童子鸡以示纪念,我也不例外。记忆中鸡是半拉大鸡仔,退好毛洗净后,置于物什中,倒入清水,加些许盐末,隔水清蒸。母亲守着柴灶,慢火炖烧,时不时用筷子戳一下,待熟了之后端上桌面倒少许自酿黄酒,招呼着你赶紧来吃。看着热气直冒,香气四溢的炖鸡,大有舍不得下筷之心。沿着碗边轻轻的嘬一口,酒香入鼻,甘味入口,其滋味,至今不能放下。
那时,由于家家户户并不宽裕,一年难得吃上几次肉,更何谈吃炖鸡。一般人家都买不起鸡(其实市场也很少有半鸡仔买),基本上家家都是自养的。为了养鸡,父母很早就开始谋划,养好母鸡多生蛋,留下好种蛋(其实蛋也很珍贵,重要的客人或遇到重要体力的事才能舍得一二)。然后选择服性、听话的母鸡抱窝,其它母鸡要抱窝,要用水浸,蒙眼站竹杆让它醒窝。窝中通常放二三十枚受精蛋。其间,要常翻蛋。到一定时期母亲还要用煤油灯照蛋,剔除不发育的部分。大约二三十天后,小鸡出壳,细心照料。十几天后,就由老母鸡带着散养,那时人都吃不饱,没有多余粮食喂养,每天清晨或傍晚,父母就常常让我们挑着鸡笼,到刚割完的稻田去放养。放开笼闸时,大小鸡们欢快地窜出鸡笼。鸡找食的同时,我们也动手捉虫、捉青蛙或游戏,边玩边收获鸡们的成长。归鸡笼时,我们拿着笼闸,轻轻赶着鸡群,嘴上轻轻哼着“归归笼,归归笼”。鸡兄鸡妹虽不情愿,倒也听话,慢吞吞一步一啄地往鸡笼里移,常有那么一两只倔点的进去后又窜出来折腾几下,看其它同伴都已归舍了,怕落单,才又急窜回去。小时记忆中,家里养鸡年年如此轮回。放养地点都是在官塘门田坌,如今想起那时的官塘门、官塘坑,以及坑坝上残损的鹅卵石路,坑边的淤泥甚厚的茭笋塘,染布坊都清晰如初,倍感亲切。尤其让人感叹如今这样常见的家禽,在那个年代是如此珍贵,以至于要让父母如此珍视,还要让我们如此精心喂养。想必其中既有当时物资匮乏的原因,更有属于父母自己的故事吧!
少时常听人讲,都快吃鸡了,还这么不懂事,也偶听母亲、兄长们讲你快有鸡吃了。后来才知道,每家孩子到了十六岁就要吃一整只童子鸡,不分男女,人人有此幸事。此一习俗的典故,据说一是童子鸡正处生命最旺盛的时期,所有部分都集中了最精华的要素,是为大补,松阳俗语“斤鸡两鳖”为大补,人们耳熟能详;二是人逢十六正是身体发育的重要节点,要抓紧补养,否则贻误发育;三是十六岁是少年与成人的分水龄,需要纪念,更需要孩子们铭记。儿时不更事,只想着有一次被父母庄重记惦的宠幸,有一次独享被父母溺爱的幸福,天天盼着这一天,担心被父母遗忘,冷不丁有一天母亲说今天杀只鸡给你吃吃,你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记得那是初三晚习回来,母亲端上用花碗盛着的炖鸡,叫我把它吃了,没有过多的表情和过多的交待,转身又忙着其它了。也许七个孩子的家庭,注定了她穷于奔波的生活状态。没有浪漫,没有仪式对她实属一种无奈。看着眼前香气扑鼻的炖鸡,朦胧中觉着自己有一种要改变些什么的冲动和又要失去些什么的惆怅。咀嚼着细滑的鸡肉,品味着浓厚的鸡汤,全然没有狼吞虎咽的急切。竟然失去了独享的欲望,虽然兄长们已经历过,父母们也绝不会分享这美味。可我仍未能享用完这顿没有庄重仪式,但又不乏内容蕴含的炖鸡宴,仍留下了不少,或许是有意为之吧?
最近一次与人闲聊中谈及这一话题,开始留意这一体验,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都感同身受。目前这一风俗仍旧良好地被传承着,当然意蕴有着微妙的变化。
几个月前的一天,丈母娘为舅子女儿烧了一只鸡仔,让我忽然明白,不经意间她已经十六岁了,赶在她外出求学前的这碗炖鸡,没有了育鸡的故事,炖鸡的行头也全然不同。从前童子鸡全是自家亲养,吃杂食,柴灶炖烧,想来味道会有较大偏差。因此她只将就尝了一丁点就搁置一旁了。或许是当今年轻人生活好了,口味也变刁了;或许是正在成为青年的他们,模糊了十六岁咥整鸡界碑式的意义,而失去了对十六岁这碗炖鸡的期待不无关系。
台湾《汉声》杂志创始人黄永松老师说:民俗最大的意义在于造就好人,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优秀民俗资源,人造就好了,民族自然就强大了。十六岁咥整鸡的民俗,没有厚重的仪式,但有着极为庄重的内涵。是一份责任的传承,是对青年人担当使命的警醒,是生命开始充满质感的起点,只要大家觉醒,十六岁咥整鸡的风俗,会永远延续。
现在想来,十六岁时,母亲端上的一碗炖鸡,意味极其悠长。
(张增明:松阳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