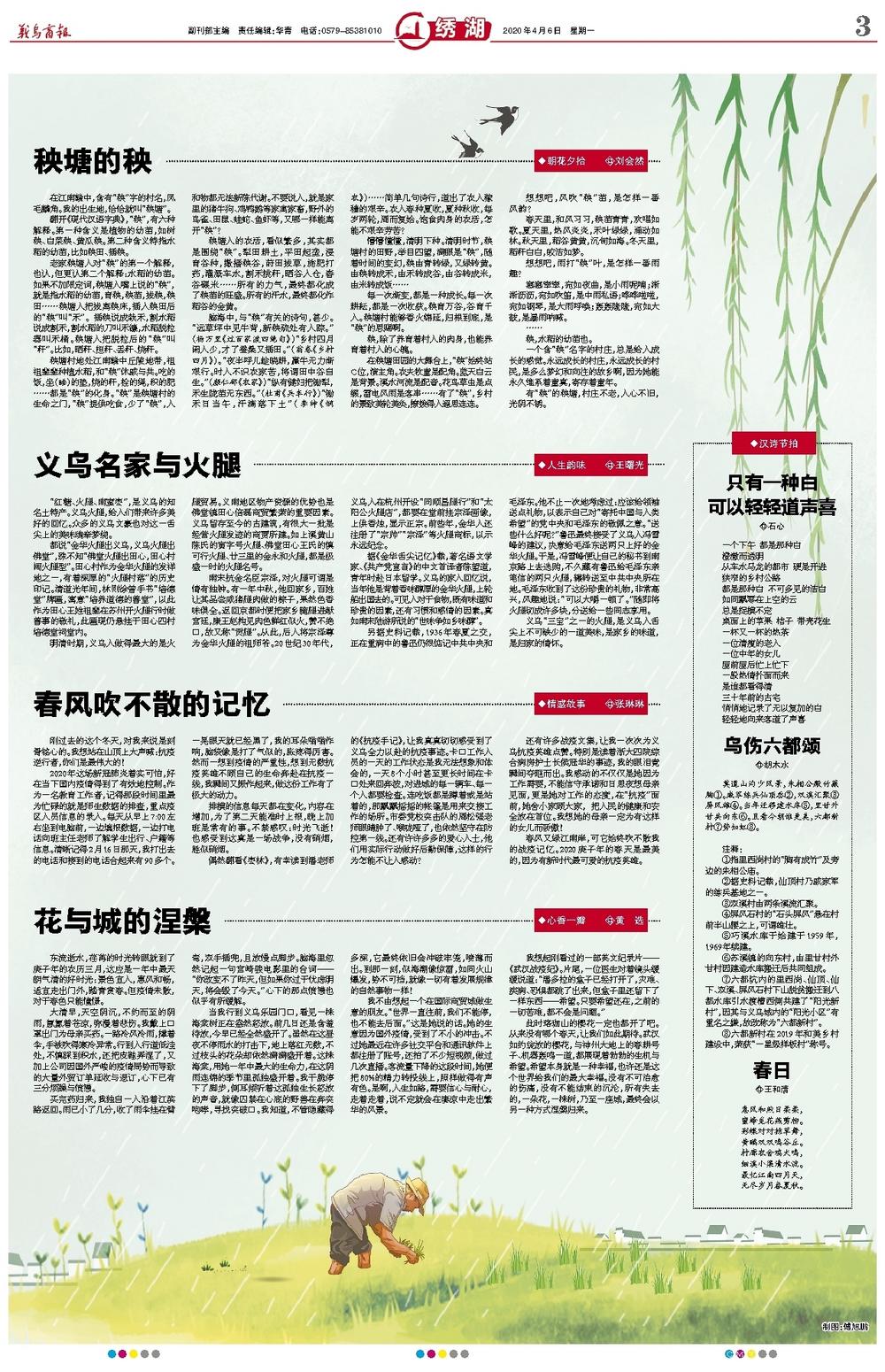在江南赣中,含有“秧”字的村名,凤毛麟角。我的出生地,恰恰就叫“秧塘”。
翻开《现代汉语字典》,“秧”,有六种解释。第一种含义是植物的幼苗,如树秧、白菜秧、黄瓜秧。第二种含义特指水稻的幼苗,比如秧田、插秧。
老家秧塘人对“秧”的第一个解释,也认,但更认第二个解释:水稻的幼苗。如果不加限定词,秧塘人嘴上说的“秧”,就是指水稻的幼苗,育秧,秧苗,拔秧,秧田……秧塘人把拔离秧床,插入秧田后的“秧”叫“禾”。 插秧说成栽禾,割水稻说成割禾,割水稻的刀叫禾镰,水稻脱粒器叫禾桶。秧塘人把脱粒后的“秧”叫“秆”。比如,晒秆、担秆、丢秆、烧秆。
秧塘村地处江南赣中丘陵地带,祖祖辈辈种植水稻,和“秧”休戚与共。吃的饭,坐(睡)的垫,烧的秆,栓的绳,积的肥……都是“秧”的化身。“秧”是秧塘村的生命之门,“秧”提供吃食,少了“秧”,人和物都无法新陈代谢。不要说人,就是家里的猪牛狗、鸡鸭鹅等家禽家畜,野外的鸟雀、田鼠、蛙蛇、鱼虾等,又哪一样能离开“秧”?
秧塘人的农活,看似繁多,其实都是围绕“秧”。犁田耕土,平田起垄,浸育谷种,撒播秧谷,莳田拔草,施肥打药,灌溉车水,割禾挑秆,晒谷入仓,舂谷碾米……所有的力气,最终都化成了秧苗的旺盛。所有的汗水,最终都化作稻谷的金黄。
脑海中,与“秧”有关的诗句,甚少。“远草坪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杨万里《过百家渡四绝句》)“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翁卷《乡村四月》)。“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颜仁郁《农家》)“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苗无东西。”(杜甫《兵车行》)“锄禾日当午,汗滴落下土”(李绅《悯农》)……简单几句诗行,道出了农人稼穑的艰辛。农人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每岁两轮,周而复始。饱食肉身的农活,怎能不艰辛劳苦?
懵懵懂懂,清明下种。清明时节,秧塘村的田野,举目四望,满眼是“秧”,随着时间的变幻,秧由青转绿,又绿转黄。由秧转成禾,由禾转成谷,由谷转成米,由米转成饭……
每一次渐变,都是一种成长。每一次耕耘,都是一次收获。秧育万谷,谷育千人。秧塘村能够香火绵延,归根到底,是“秧”的恩赐啊。
秧,除了养育着村人的肉身,也能养育着村人的心魄。
在秧塘田园的大舞台上,“秧”始终站C位,演主角。农夫牧童是配角。蓝天白云是背景。溪水河流是配音。花鸟草虫是点缀,雷电风雨是客串……有了“秧”,乡村的景致美轮美奂,撩拨得人遐思连连。
想想吧,风吹“秧”苗,是怎样一番风韵?
春天里,和风习习,秧苗青青,欢唱如歌。夏天里,热风炎炎,禾叶绿绿,涌动如林。秋天里,稻谷黄黄,沉甸如海。冬天里,稻秆白白,皎洁如梦。
想想吧,雨打“秧”叶,是怎样一番雨趣?
窸窸窣窣,宛如夜曲,是小雨呢喃;淅淅沥沥,宛如吹笛,是中雨私语;哗哗啦啦,宛如钢琴,是大雨呼唤;轰轰隆隆,宛如大鼓,是暴雨呐喊。
……
秧,水稻的幼苗也。
一个含“秧”名字的村庄,总是给人成长的感觉。永远成长的村庄,永远成长的村民,是多么梦幻和向往的故乡啊,因为她能永久维系着童真,寄存着童年。
有“秧”的秧塘,村庄不老,人心不旧,光阴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