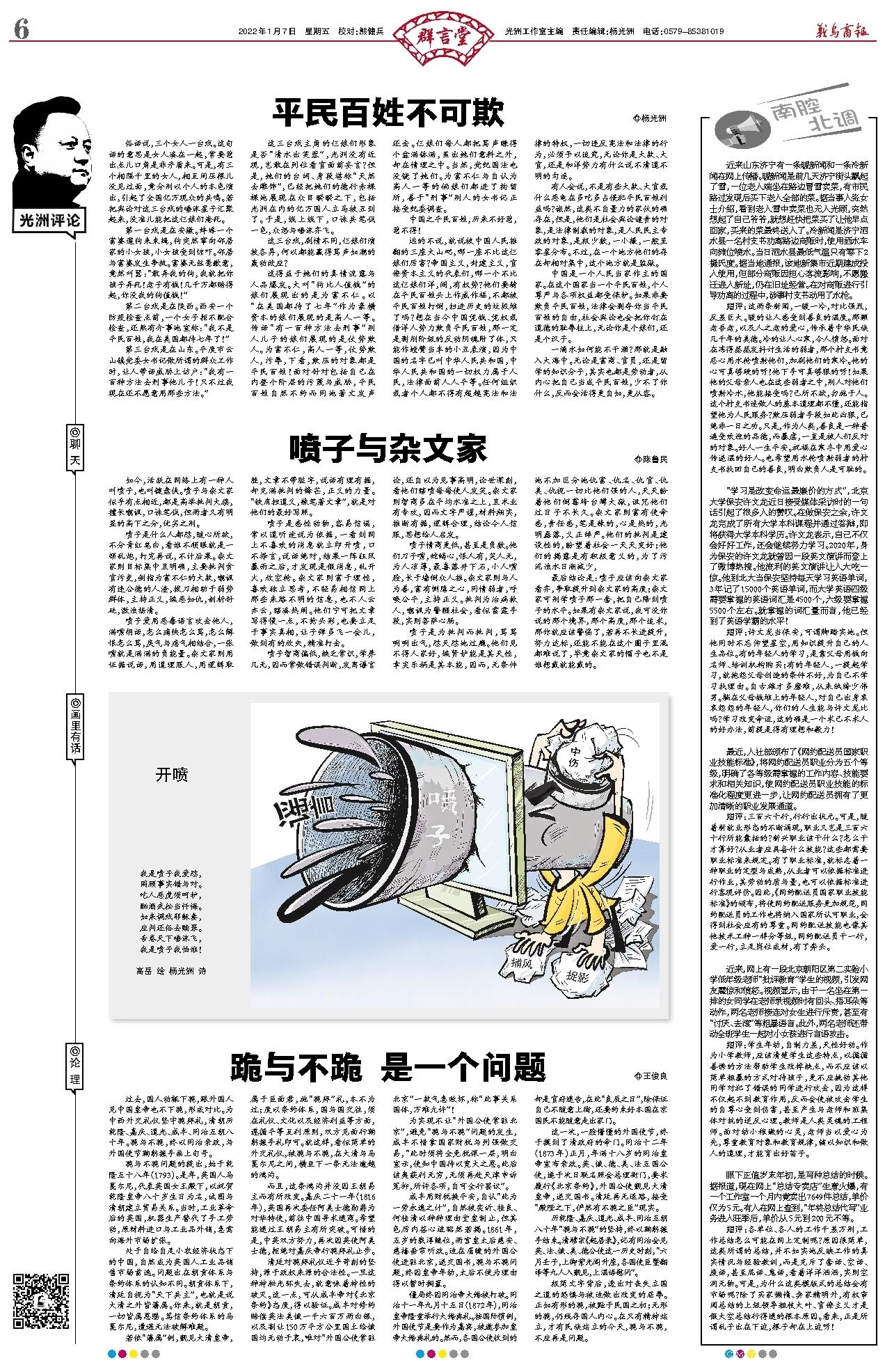过去,国人动辄下跪,跟外国人见中国皇帝也不下跪,形成对比。为中西外交礼仪坚守跪拜礼,清朝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八十年。跪与不跪,终以同治亲政,与外国使节鞠躬握手画上句号。
跪与不跪问题的提出,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是年,英国人马戛尔尼,代表英国女王殿下,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为名,试图与清朝建立贸易关系。当时,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劳动,原材料进口与工业品外销,急需向海外市场扩张。
处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自然成为英国人工业品销售市场首选。问题出在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认知不同。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也就是说大清之外皆藩属。你来,就是朝贡,一切皆属恩赐。笃信条约体系的马戛尔尼,遭遇无法破解难题。
若依“藩属”例,觐见大清皇帝,属于臣面君,施“跪拜”礼,本不为过;度以条约体系,国与国交往,须在礼仪、文化以及经济利益等方面,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双方见面行鞠躬握手礼即可。就这样,看似简单的外交礼仪,被跪与不跪,在大清与马戛尔尼之间,横亘下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且,这条鸿沟并没因王朝易主而有所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委任阿美士德勋爵为对华特使,前往中国寻求通商。希望能通过王朝易主有所突破。可惜的是,中英双方努力,再次因英使阿美士德,拒绝对嘉庆帝行跪拜礼止步。
清廷对跪拜礼仪近乎苛刻的坚持,源于政权来源的合法性。一旦这种神秘光环失去,就意味着神性的破灭。这一点,可从咸丰帝对《北京条约》态度,得以验证。咸丰对修约赔偿英法美俄一千六百万两白银,以及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给俄国均无动于衷,唯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一款气急败坏,称“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为实现不让“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避免“跪与不跪”问题的发生,咸丰不惜拿国家财税与列强做交易,“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申诉冤抑,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
咸丰用财税换平安,自认“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自然被奕、桂良、何桂清以种种理由堂皇制止,但其色厉内荏心迹昭然若揭。1861年,五岁的载淳继位,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迫在眉睫的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递交国书,跪与不跪问题,终因皇帝年幼,太后不便为理由得以暂时搁置。
僵局终因同治帝大婚被打破。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同治皇帝隆重举行大婚典礼。按国际惯例,外国使节是要作为嘉宾,被邀参加皇帝大婚典礼的。然而,各国公使收到的却是官府通告,在此“良辰之日”,除保证自己不随意上街,还要约束好本国在京国民不能随意走出家门。
这一次,一脸懵懂的外国使节,终于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年满十八岁的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遂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履行《北京条约》,外国公使觐见大清皇帝,递交国书。清廷再无退路,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现实。
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八十年“跪与不跪”的坚持,终以鞠躬握手结束。清穆宗《起居录》,记有同治会见英、法、俄、美、德公使这一历史时刻,“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极简文字背后,透出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正如有形的跪,被黜于民国之初;无形的跪,仍残存国人内心。在只有精神站立,才有民族站立的今天,跪与不跪,不应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