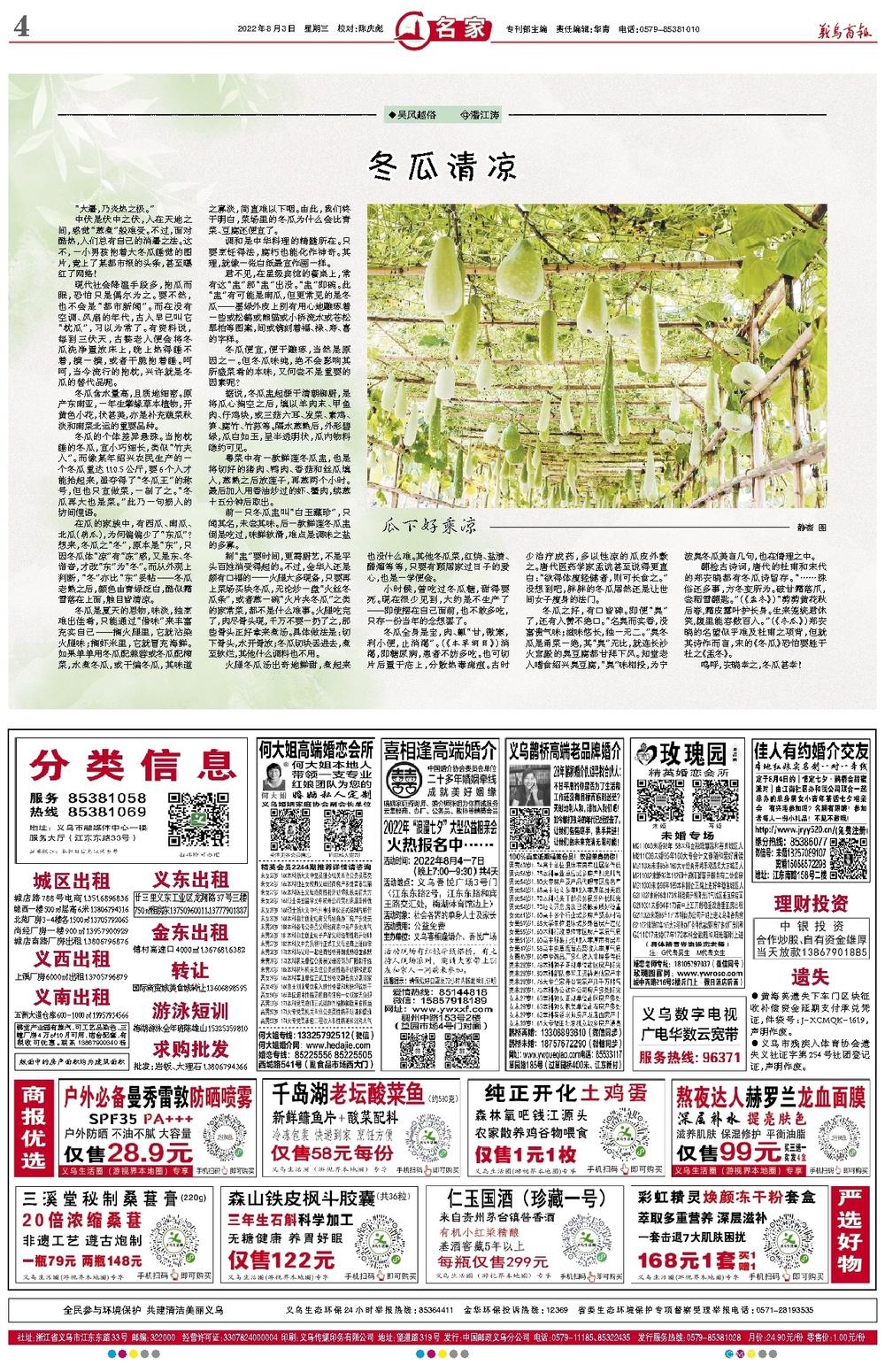“大暑,乃炎热之极。”
中伏是伏中之伏,人在天地之间,感觉“蒸煮”般难受。不过,面对酷热,人们总有自己的消暑之法。这不,一小男孩抱着大冬瓜睡觉的图片,竟上了某都市报的头条,甚至曝红了网络!
现代社会降温手段多,抱瓜而眠,恐怕只是偶尔为之。要不然,也不会是“都市新闻”。而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年代,古人早已叫它“枕瓜”,习以为常了。有资料说,每到三伏天,古婺老人便会将冬瓜洗净置放床上,晚上热得睡不着,摸一摸,或者干脆抱着睡。呵呵,当今流行的抱枕,兴许就是冬瓜的替代品呢。
冬瓜含水量高,且质地细密。原产东南亚,一年生攀缘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状甚美,亦是补充蔬菜秋淡和南菜北运的重要品种。
冬瓜的个体差异悬殊。当抱枕睡的冬瓜,宜小巧细长,类似“竹夫人”。而像某年绍兴农民生产的一个冬瓜重达110.5公斤,要6个人才能抬起来,虽夺得了“冬瓜王”的称号,但也只宜做菜,一剖了之。“冬瓜再大也是菜。”此乃一句损人的坊间俚语。
在瓜的家族中,有西瓜、南瓜、北瓜(葫瓜),为何偏偏少了“东瓜”?想来,冬瓜之“冬”,原本是“东”,只因冬瓜体“凉”有“冻”感,又是东、冬谐音,才改“东”为“冬”。而从外观上判断,“冬”亦比“东”妥帖——冬瓜老熟之后,颜色由青绿泛白,酷似霜雪落在上面,触目皆清凉。
冬瓜是夏天的恩物,味淡,独烹难出佳肴,只能通过“借味”来丰富充实自己——搁火腿里,它就沾染火腿味;搁虾米里,它就冒充海鲜。如果单单用冬瓜配蒜蓉或冬瓜配榨菜,水煮冬瓜,或干煸冬瓜,其味道之寡淡,简直难以下咽。由此,我们终于明白,菜场里的冬瓜为什么会比青菜、豆腐还便宜了。
调和是中华料理的精髓所在。只要烹饪得法,腐朽也能化作神奇。其理,就像一张白纸最宜作画一样。
君不见,在星级宾馆的餐桌上,常有这“盅”那“盅”出没。“盅”即碗。此“盅”有可能是南瓜,但更常见的是冬瓜——墨绿外皮上别有用心地雕琢着一些或松鹤或熊猫或小桥流水或苍松翠柏等图案,间或镌刻着福、禄、寿、喜的字样。
冬瓜便宜,便于雕琢,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冬瓜味纯,绝不会影响其所盛菜肴的本味,又何尝不是重要的因素呢?
据说,冬瓜盅起源于清朝御厨,是将瓜心掏空之后,填以羊肉末、甲鱼肉、仔鸡块,或三菇六耳、发菜、素鸡、笋、腐竹、竹荪等。隔水蒸熟后,外形碧绿,瓜白如玉,呈半透明状,瓜内物料隐约可见。
粤菜中有一款鲜莲冬瓜盅,也是将切好的猪肉、鸭肉、香菇和丝瓜填入,蒸熟之后放莲子,再蒸两个小时。最后加入用香油炒过的虾、蟹肉,续蒸十五分钟后取出。
前一只冬瓜盅叫“白玉藏珍”,只闻其名,未尝其味。后一款鲜莲冬瓜盅倒是吃过,味鲜软滑,难点是调味之盐的多寡。
制“盅”要时间,更需厨艺,不是平头百姓消受得起的。不过,金华人还是颇有口福的──火腿大多现备,只要再上菜场买块冬瓜,无论炒一盘“火丝冬瓜条”,或者蒸一碗“火片夹冬瓜”之类的家常菜,都不是什么难事。火腿吃完了,肉尽骨头现,千万不要一扔了之,那些骨头正好拿来煮汤。具体做法是:切下骨头,水开骨放;冬瓜切块丢进去,煮至软烂,其他什么调料也不用。
火腿冬瓜汤出奇地鲜甜,煮起来也没什么难。其他冬瓜菜,红烧、盐渍、醋熘等等,只要有颗居家过日子的爱心,也是一学便会。
小时候,曾吃过冬瓜糖,甜得要死。现在很少见到,大约是不生产了——即使摆在自己面前,也不敢多吃,只存一份当年的念想罢了。
冬瓜全身是宝,肉、瓤“甘,微寒,利小便,止消渴”。(《本草纲目》)消渴,即糖尿病,患者不妨多吃。也可切片后置于疮上,分散热毒痈疽。古时少治疗成药,多以性凉的瓜皮外敷之。唐代医药学家孟诜甚至说得更直白:“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没想到吧,胖胖的冬瓜居然还是让世间女子瘦身的法门。
冬瓜之好,有口皆碑。即便“臭”了,还有人赞不绝口。“名臭而实香,没富贵气味;滋味悠长,独一无二。”臭冬瓜是甬菜一绝,其“臭”无比,就连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都甘拜下风。知堂老人嗜食绍兴臭豆腐,“臭”味相投,为宁波臭冬瓜美言几句,也在情理之中。
翻检古诗词,唐代的杜甫和宋代的郑安晓都有冬瓜诗留存。“……殊俗还多事,方冬变所为。破甘霜落爪,尝稻雪翻匙。”(《孟冬》)“剪剪黄花秋后春,霜皮露叶护长身。生来笼统君休笑,腹里能容数百人。”(《冬瓜》)郑安晓的名望似乎难及杜甫之项背,但就其诗作而言,宋的《冬瓜》恐怕要胜于杜之《孟冬》。
呜呼,安晓幸之,冬瓜甚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