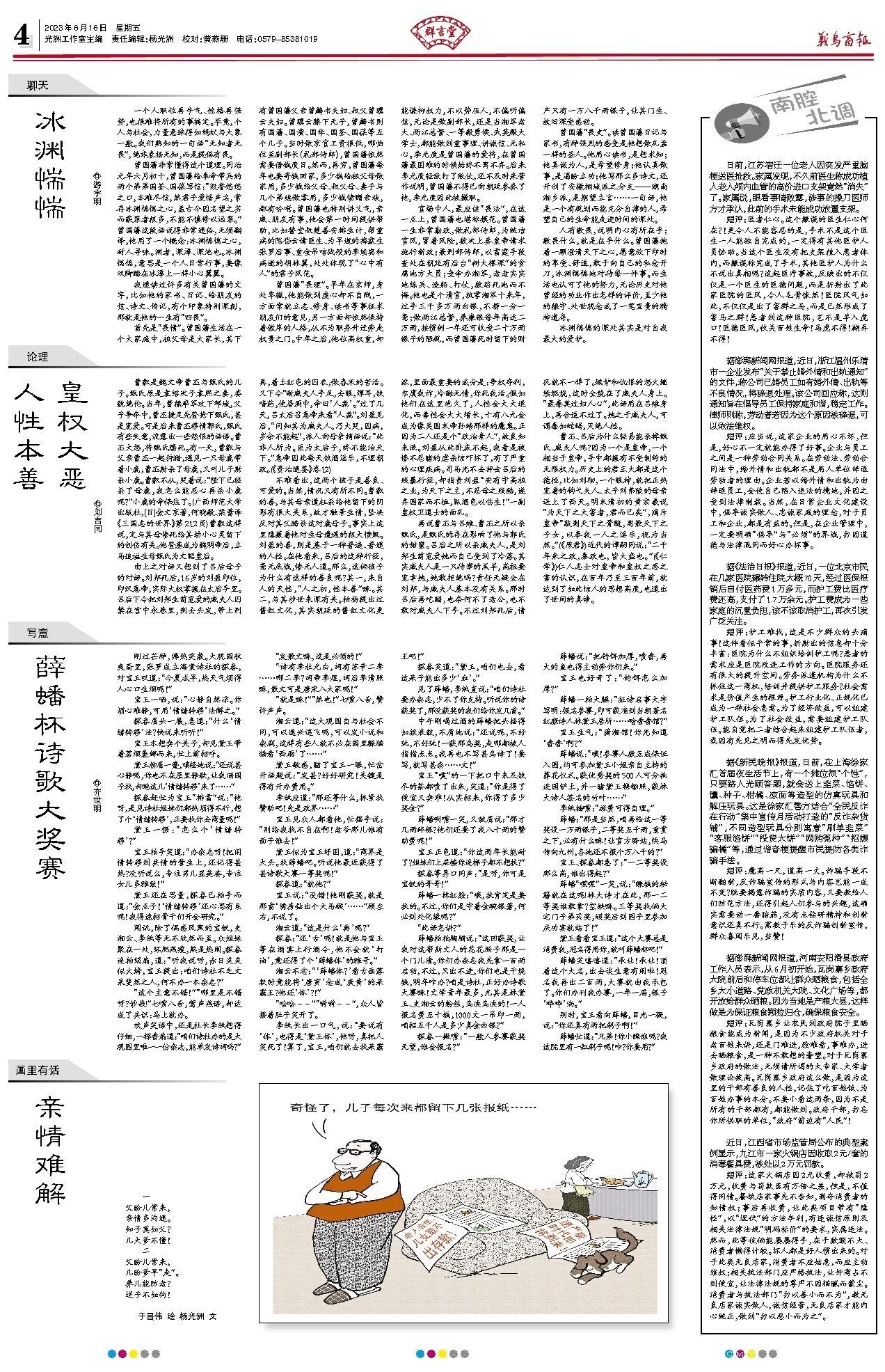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甄氏的儿子。甄氏原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姿貌绝伦。当年,曹操率军攻下邺城,父子争夺中,曹丕捷足先登抢下甄氏,甚是宠爱。可是后来曹丕移情郭氏,甄氏有些失意,流露出一些怨恨的话语。曹丕大怒,将甄氏赐死。有一天,曹叡与父亲曹丕一起狩猎,遇见一只母鹿带着小鹿,曹丕射杀了母鹿,又叫儿子射杀小鹿。曹叡不从,哭着说:“陛下已经杀了母鹿,我怎么能忍心再杀小鹿呢?”小鹿的命保住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日]金文京著,何晓毅、梁蕾译《三国志的世界》第212页)曹叡这样说,定与其母惨死给其幼小心灵留下的创伤有关。他登基成为魏明帝后,立马追谥生母甄氏为文昭皇后。
由上之对话又想到了吕后母子的对话。刘邦死后,16岁的刘盈即位,即汉惠帝,实际大权掌握在太后手里。吕后下令把刘邦生前宠爱的戚夫人囚禁在宫中永巷里,剃去头发,带上刑具,着土红色的囚衣,做舂米的苦活。又下令“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过了几天,吕太后召惠帝来看“人彘”。刘盈见后,“问知其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派人向母亲捎话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惠帝因此每天饮酒淫乐,不理朝政。(《资治通鉴》卷12)
不难看出,这两个孩子是善良、可爱的。当然,情况又有所不同。曹叡的善,与其母亲遭枉杀给他留下的阴影有很大关系,故才触景生情,坚决反对其父猎杀这对鹿母子。事实上这里隐藏着他对生母遭遇的极大愤慨。刘盈的善,则是基于一种普遍、普通的人性。在他看来,吕后的这种行径,毫无底线,惨无人道。那么,这俩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善良呢?其一,来自人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其二,与其涉世未深有关。柏杨提出过酱缸文化,其实朝廷的酱缸文化更浓,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冷酷无情,你死我活。假如他们在这里泡久了,人性会大大退化,而兽性会大大增长,十有八九会成为像吴国末帝孙皓那样的魔鬼。正因为二人还是个“政治素人”,故良知未泯。刘盈从此卧床不起,我看是被惨不忍睹的虐杀惊吓坏了,有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司马光不去抨击吕后的残暴行径,却指责刘盈“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一副皇权卫道士的面孔。
再说曹丕与吕雉、曹丕之所以杀甄氏,是甄氏的存在影响了他与郭氏的甜蜜。吕后之所以杀戚夫人,是刘邦生前宠爱她而自己受到了冷落。其实戚夫人是一只待宰的羔羊,高祖要宠幸她,她敢拒绝吗?责任无疑全在刘邦,与戚夫人基本没有关系。那时吕后再吃醋,也奈何不了老公,也不敢对戚夫人下手。不过刘邦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嫉妒和仇恨的怒火继续燃烧,这时全烧在了戚夫人身上。“最毒莫过妇人心”,此话用在吕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她之于戚夫人,可谓毒如蛇蝎,灭绝人性。
曹丕、吕后为什么轻易能杀掉甄氏、戚夫人呢?因为一个是皇帝,一个相当于皇帝,手中都握有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历史上的君王大都是这个德性,比如刘彻,一个眼神,就把正热宠着的钩弋夫人、太子刘弗陵的母亲送上了西天。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痛斥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原君》)近代的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仁人志士对皇帝和皇权之恶之害的认识,在百年乃至三百年前,就达到了如此惊人的思想高度,也道出了世间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