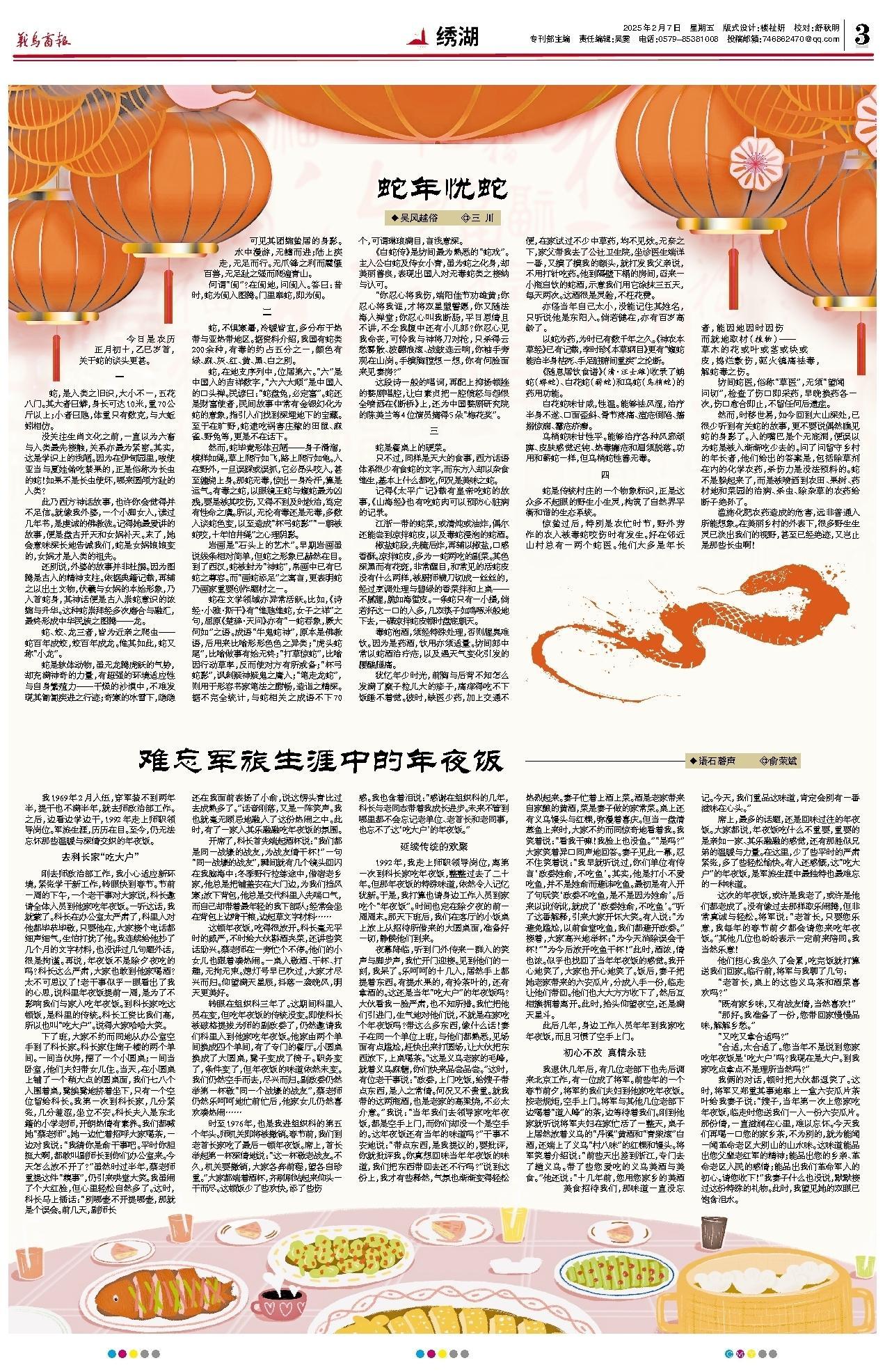今日是农历正月初十,乙巳岁首,关于蛇的谈头更甚。
一
蛇,是人类之旧识,大小不一,五花八门。其大者曰蟒,身长可达10米,重70公斤以上;小者曰虺,体重只有数克,与大蚯蚓相仿。
没关注生肖文化之前,一直以为六畜与人类最先接触,关系亦最为紧密。其实,这是学识上的浅陋。因为在伊甸园里,唆使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的,正是俗称为长虫的蛇!如果不是长虫使坏,哪来圆颅方趾的人类?
此乃西方神话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并不足信。就像我外婆,一个小脚女人,读过几年书,是虔诚的佛教徒。记得她最爱讲的故事,便是盘古开天和女娲补天。末了,她会意味深长地告诫我们,蛇是女娲娘娘变的,女娲才是人类的祖先。
还别说,外婆的故事并非杜撰。因为图腾是古人的精神支柱。依据典籍记载,再辅之以出土文物,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乃人首蛇身,其神话便是古人崇蛇意识的浓缩与升华。这种蛇崇拜经多次磨合与融汇,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之图腾——龙。
蛇、蛟、龙三者,皆为近亲之爬虫——蛇百年成蛟,蛟百年成龙。惟其如此,蛇又称“小龙”。
蛇是软体动物,虽无龙腾虎跃的气势,却充满神奇的力量,有超强的环境适应性与自身繁殖力——干燥的沙漠中,不难发现其匍匐疾进之行迹;奇寒的冰雪下,隐隐可见其团缩蛰居的身影。水中漫游,无鳍而进;陆上疾走,无足而行。无爪锋之利而震慑百兽,无足趾之强而爬遍青山。
何谓“闽”?在闽地,问闽人。答曰:昔时,蛇为闽人图腾。门里奉蛇,即为闽。
二
蛇,不惧寒暑,冷暖皆宜,多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据资料介绍,我国有蛇类200余种,有毒的约占五分之一,颜色有绿、麻、灰、红、黄、黑、白之别。
蛇,在地支序列中,位居第六。“六”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六六大顺”是中国人的口头禅。民谚曰:“蛇盘兔,必定富”。蛇还是财富使者,民间故事中常有金银幻化为蛇的意象,指引人们找到深埋地下的宝藏。至于在旷野,蛇逮吃祸害庄稼的田鼠、麻雀、野兔等,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蛇毕竟形体丑陋——身子滑溜,模样如绳,草上爬行如飞,路上爬行如龟。人在野外,一旦误踩或误抓,它必昂头咬人,甚至缠绕上身。那蛇无毒,惊出一身冷汗,算是运气。有毒之蛇,以眼镜王蛇与蝮蛇最为凶残,要是被其咬伤,又得不到及时救治,笃定有性命之虞。所以,无论有毒还是无毒,多数人谈蛇色变,以至造成“杯弓蛇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心理阴影。
岩画是“石头上的艺术”。早期岩画虽说线条相对简单,但蛇之形象已赫然在目。到了西汉,蛇被封为“神蛇”,帛画中已有巳蛇之尊容。而“画蛇添足”之寓言,更表明蛇乃画家重要创作题材之一。
蛇在文学领域亦异常活跃。比如,《诗经·小雅·斯干》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之句,屈原《楚辞·天问》亦有“一蛇吞象,厥大何如”之语。成语“牛鬼蛇神”,原本是佛教语,后用来比喻形形色色之异类;“虎头蛇尾”,比喻做事有始无终;“打草惊蛇”,比喻因行动草率,反而使对方有所戒备;“杯弓蛇影”,讽刺疑神疑鬼之庸人;“笔走龙蛇”,则用于形容书家笔法之酣畅,造诣之精深。据不完全统计,与蛇相关之成语不下70个,可谓琳琅满目,言浅意深。
《白蛇传》是坊间最为熟悉的“蛇戏”。主人公白蛇及侍女小青,虽为蛇之化身,却美丽善良,表现出国人对无毒蛇类之接纳与认可。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劝雄黄;你忍心将我诓,才将双星盟誓愿,你又随法海入禅堂;你忍心叫我断肠,平日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还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命丧,可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波翻浪滚、战鼓连云响,你袖手旁观在山岗。手摸胸膛想一想,你有何脸面来见妻房?”
这段诗一般的唱词,再配上抑扬顿挫的婺剧唱腔,让白素贞把一腔愤怒与怨恨全喷洒在《断桥》上,还为中国婺剧研究院的陈美兰等4位演员摘得5朵“梅花奖”。
三
蛇是餐桌上的硬菜。
只不过,同样是天大的食事,西方话语体系很少有食蛇的文字,而东方人却以杂食维生,基本上什么都吃,何况是美味之蛇。
记得《太平广记》载有皇帝吃蛇的故事,《山海经》也有吃蛇肉可以预防心脏病的记录。
江浙一带的蛇菜,或清炖或油炸,偶尔还能尝到凉拌蛇皮,以及毒蛇浸泡的蛇酒。
椒盐蛇段,先腌后炸,再辅以椒盐,口感香酥。凉拌蛇皮,多为一蛇两吃的副菜。其色深黑而有花斑,非常醒目,和常见的活蛇皮没有什么两样,被厨师横刀切成一丝丝的,经过烹调处理与碧绿的香菜拌和上桌——不腻腥,脆如海蜇皮。一条蛇只有一小撮,倘若好这一口的人多,几双筷子如鸡啄米般地下去,一碟凉拌蛇皮顿时盘底朝天。
毒蛇泡酒,须经特殊处理,否则腥臭难饮。因为是药酒,饮用亦须适量。坊间郎中常以蛇酒治疔疮,以及遇天气变化引发的腰酸腿痛。
犹忆年少时光,前胸与后背不知怎么发满了糜子粒儿大的疹子,痛痒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彼时,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在家试过不少中草药,均不见效。无奈之下,家父带我去了公社卫生院,坐诊医生端详一番,又摸了摸我的额头,就打发我父亲说,不用打针吃药。他到隔壁下榻的房间,舀来一小瓶自饮的蛇酒,示意我们用它涂抹三五天,每天两次。这酒很是灵验,不枉花费。
亦怪当年自己太小,没能记住其姓名,只听说他是东阳人。倘若健在,亦有百岁高龄了。
以蛇为药,为时已有数千年之久。《神农本草经》已有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更有“蝮蛇能治半身枯死、手足脏腑间重疾”之论断。
《随息居饮食谱》(清·汪士雄)收录了蚺蛇(蟒蛇)、白花蛇(蕲蛇)和乌蛇(乌梢蛇)的药用功能。
白花蛇味甘咸,性温。能够祛风湿,治疗半身不遂、口面歪斜、骨节疼痛、痘疮倒陷、搐搦惊痫、霉疮疥癣。
乌梢蛇味甘性平。能够治疗各种风邪顽痹、皮肤感觉迟钝、热毒癞疮和眉须脱落。功用和蕲蛇一样,但乌梢蛇性善无毒。
四
蛇是传统村庄的一个物象标识,正是这众多不起眼的野生小生灵,构筑了自然界平衡和谐的生态系统。
惊蛰过后,特别是农忙时节,野外劳作的农人被毒蛇咬伤时有发生。好在邻近山村总有一两个蛇医。他们大多是年长者,能因地因时因伤而就地取材(植物)——草木的花或叶或茎或块或皮,捣烂敷伤,驱火镇痛祛毒,解蛇毒之伤。
坊间蛇医,俗称“草医”,无须“望闻问切”,检查了伤口即采药,早晚换药各一次,伤口愈合即止,不留任何后遗症。
然而,时移世易,如今回到大山深处,已很少听到有关蛇的故事,更不要说偶然瞧见蛇的身影了。人的嘴巴是个无底洞,便误以为蛇是被人渐渐吃少去的。问了问留守乡村的年长者,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包括除草剂在内的化学农药,杀伤力是没法预料的。蛇不是躲起来了,而是被喷洒到农田、果树、药材地和菜园的治病、杀虫、除杂草的农药给断子绝孙了。
滥施化肥农药造成的危害,远非普通人所能想象。在美丽乡村的外表下,很多野生生灵已淡出我们的视野,甚至已经绝迹,又岂止是那些长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