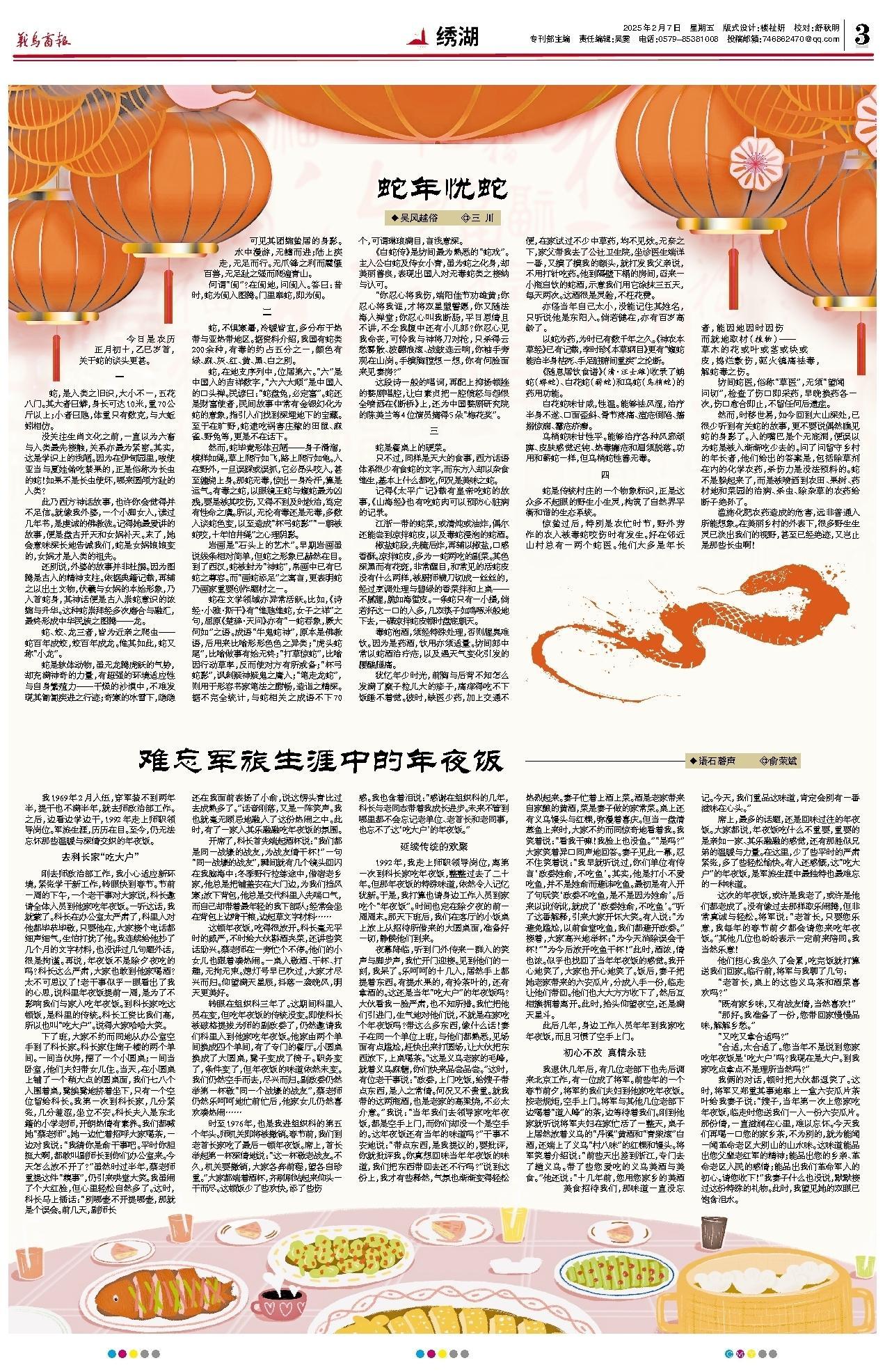我1969年2月入伍,穿军装不到两年半,提干也不满半年,就去师政治部工作。之后,边看边学边干,1992年走上师职领导岗位。军旅生涯,历历在目。至今,仍无法忘怀那些温暖与深情交织的年夜饭。
去科长家“吃大户”
刚去师政治部工作,我小心适应新环境,紧张学干新工作,转眼快到春节。节前一周的下午,一个老干事对大家说,科长邀请全体人员到他家吃年夜饭。一听这话,我就蒙了。科长在办公室太严肃了,科里人对他都毕恭毕敬,只要他在,大家接个电话都细声细气,生怕打扰了他。我连续给他抄了几个月的文字材料,也没讲过几句题外话,很是拘谨。再说,年夜饭不是除夕夜吃的吗?科长这么严肃,大家也敢到他家喝酒?太不可思议了!老干事似乎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说科里年夜饭提前一周,是为了不影响我们与家人吃年夜饭。到科长家吃这顿饭,是科里的传统。科长工资比我们高,所以也叫“吃大户”。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下了班,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办公室空手到了科长家。科长家住筒子楼的两个单间。一间当伙房,摆了一个小圆桌;一间当卧室,他们夫妇带女儿住。当天,在小圆桌上铺了一个稍大点的圆桌面,我们七八个人围着桌,凳挨凳地挤着坐下,只有一个空位留给科长。我第一次到科长家,几分紧张,几分羞涩,坐立不安。科长夫人是东北籍的小学老师,开朗热情有素养。我们都喊她“蔡老师”。她一边忙着招呼大家喝茶,一边对我说:“我猜你是俞干事吧。平时你胆挺大啊,都敢叫副师长到你们办公室来。今天怎么放不开了?”虽然时过半年,蔡老师重提这件“糗事”,仍引来哄堂大笑。我虽闹了个大红脸,但心里轻松自然多了。这时,科长马上插话:“别哪壶不开提哪壶,那就是个误会。前几天,副师长还在我面前表扬了小俞,说这愣头青比过去成熟多了。”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笑声。我也就毫无顾忌地融入了这份热闹之中。此时,有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年夜饭的氛围。
开席了,科长首先端起酒杯说:“我们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为战友情干杯!”一句“同一战壕的战友”,瞬间就有几个镜头回闪在我脑海中:冬季野行拉练途中,借宿老乡家,他总是把铺盖安在大门边,为我们挡风寒;放下背包,他总是交代科里人先喘口气,而自己却带着最年轻的我下部队;经常会坐在背包上边啃干粮,边起草文字材料……
这顿年夜饭,吃得很放开。科长毫无平时的威严,不时给大伙斟酒夹菜,还讲些笑话助兴。蔡老师在一旁忙个不停。他们的小女儿也跟着凑热闹。一桌人敬酒、干杯、打趣,无拘无束。熄灯号早已吹过,大家才尽兴而归。仰望满天星辰,抖落一袭晚风,明天更美好。
转眼在组织科三年了。这期间科里人员在变,但吃年夜饭的传统没变。即使科长被破格提拔为师的副政委了,仍然邀请我们科里人到他家吃年夜饭。他家由两个单间换成四个单间,有了专门的餐厅。小圆桌换成了大圆桌,凳子变成了椅子。职务变了,条件变了,但年夜饭的味道依然未变。我们仍然空手而去,尽兴而归。副政委仍然举第一杯敬“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蔡老师仍然乐呵呵地忙前忙后,他家女儿仍然喜欢凑热闹……
时至1976年,也是我进组织科的第五个年头。师机关即将被撤销。春节前,我们到老首长家吃了最后一顿年夜饭。席上,首长举起第一杯深情地说:“这一杯敬老战友。不久,机关要撤销,大家各奔前程,望各自珍重。”大家都端着酒杯,齐刷刷站起来仰头一干而尽。这顿饭少了些欢快,添了些伤感。我也含着泪说:“感谢在组织科的几年,科长与老同志带着我成长进步。未来不管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老单位、老首长和老同事,也忘不了这‘吃大户’的年夜饭。”
延续传统的欢聚
1992年,我走上师职领导岗位,离第一次到科长家吃年夜饭,整整过去了二十年。但那年夜饭的特殊味道,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于是,我打算也请身边工作人员到家吃个“年夜饭”。时间也定在除夕夜的前一周周末。那天下班后,我们在客厅的小饭桌上放上从招待所借来的大圆桌面,准备好一切,静候他们到来。
夜幕降临,听到门外传来一群人的笑声与脚步声,我忙开门迎接。见到他们的一刻,我呆了。乐呵呵的十几人,居然手上都提着东西。有提水果的,有拎茶叶的,还有拿酒的。这还是当年“吃大户”的年夜饭吗?大伙看我一脸严肃,也不知所措。我忙把他们引进门,生气地对他们说,不就是在家吃个年夜饭吗?带这么多东西,像什么话!妻子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与他们都熟悉,见场面有点尴尬,赶快出来打圆场,让大伙把东西放下,上桌喝茶。“这是义乌老家的毛峰,就着义乌麻糖,你们快来品尝品尝。”这时,有位老干事说:“政委,上门吃饭,给嫂子带点东西,是人之常情。何况又不贵重。就我带的这两瓶酒,也是老家的高粱烧,不必太介意。”我说:“当年我们去领导家吃年夜饭,都是空手上门,而你们却没一个是空手的。这年夜饭还有当年的味道吗?”干事不安地说:“带点东西,是我提议的,要批评,你就批评我。你真想回味当年年夜饭的味道,我们把东西带回去还不行吗?”说到这份上,我才有些释然,气氛也渐渐变得轻松热烈起来。妻子忙着上酒上菜。酒是老家带来自家酿的黄酒,菜是妻子做的家常菜。桌上还有义乌馒头与红粿,弥漫着喜庆。但当一盘清蒸鱼上来时,大家不约而同惊奇地看着我。我笑着说:“看我干嘛!我脸上也没鱼。”“是吗?”大家笑着异口同声地回答。妻子见此一幕,忍不住笑着说:“我早就听说过,你们单位有传言‘政委姓俞,不吃鱼’。其实,他是打小不爱吃鱼,并不是姓俞而避讳吃鱼。最初是有人开了句玩笑‘政委不吃鱼,是不是因为姓俞’。后来以讹传讹,就成了‘政委姓俞,不吃鱼’。”听了这番解释,引来大家开怀大笑。有人说:“为避免尴尬,以前食堂吃鱼,我们都避开政委。”接着,大家高兴地举杯:“为今天消除误会干杯!”“为今后放开吃鱼干杯!”此时,酒浓,情也浓。似乎也找回了当年年夜饭的感觉。我开心地笑了,大家也开心地笑了。饭后,妻子把她老家带来的六安瓜片,分成人手一份,临走让他们带回。他们也大大方方收下了,然后互相簇拥着离开。此时,抬头仰望夜空,还是满天星斗。
此后几年,身边工作人员年年到我家吃年夜饭,而且习惯了空手上门。
初心不改 真情永驻
我退休几年后,有几位老部下也先后调来北京工作,有一位成了将军。前些年的一个春节前夕,将军约我们夫妇到他家吃年夜饭。按老规矩,空手上门。将军与其他几位老部下边喝着“道人峰”的茶,边等待着我们。刚到他家就听说将军夫妇在家忙活了一整天,桌子上居然放着义乌的“丹溪”黄酒和“青柴滚”白酒,还端上了义乌“村八味”的红粿和馒头。将军笑着介绍说:“前些天出差到浙江,专门去了趟义乌。带了些您爱吃的义乌美酒与美食。”他还说:“十几年前,您用您家乡的美酒美食招待我们,那味道一直没忘记。今天,我们重品这味道,肯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席上,最多的话题,还是回味过往的年夜饭。大家都说,年夜饭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亲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感觉,还有那胜似兄弟的温暖与力量。在这里,少了些平时的严肃紧张,多了些轻松愉快。有人还感慨,这“吃大户”的年夜饭,是军旅生涯中最独特也最难忘的一种味道。
这次的年夜饭,或许是我老了,或许是他们都老成了。没有像过去那样取乐闹腾,但非常真诚与轻松。将军说:“老首长,只要您乐意,我每年的春节前夕都会请您来吃年夜饭。”其他几位也纷纷表示一定前来陪同。我当然乐意!
他们担心我坐久了会累,吃完饭就打算送我们回家。临行前,将军与我聊了几句:
“老首长,桌上的这些义乌茶和酒菜喜欢吗?”
“既有家乡味,又有战友情,当然喜欢!”
“那好。我准备了一份,您带回家慢慢品味,解解乡愁。”
“又吃又拿合适吗?”
“合适,太合适了。您当年不是说到您家吃年夜饭是‘吃大户’吗?我现在是大户。到我家吃点拿点不是理所当然吗?”
我俩的对话,顿时把大伙都逗笑了。这时,将军又郑重其事地奉上一盒六安瓜片茶叶给我妻子说:“嫂子,当年第一次上您家吃年夜饭,临走时您送我们一人一份六安瓜片。那份情,一直滋润在心里,难以忘怀。今天我们再喝一口您的家乡茶,不为别的,就为能闻一闻革命老区大别山的山水味。这味道能品出您父辈老红军的精神;能品出您的乡亲、革命老区人民的感情;能品出我们革命军人的初心。请您收下!”我妻子什么也没说,默默接过这份特殊的礼物。此时,我望见她的双眼已饱含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