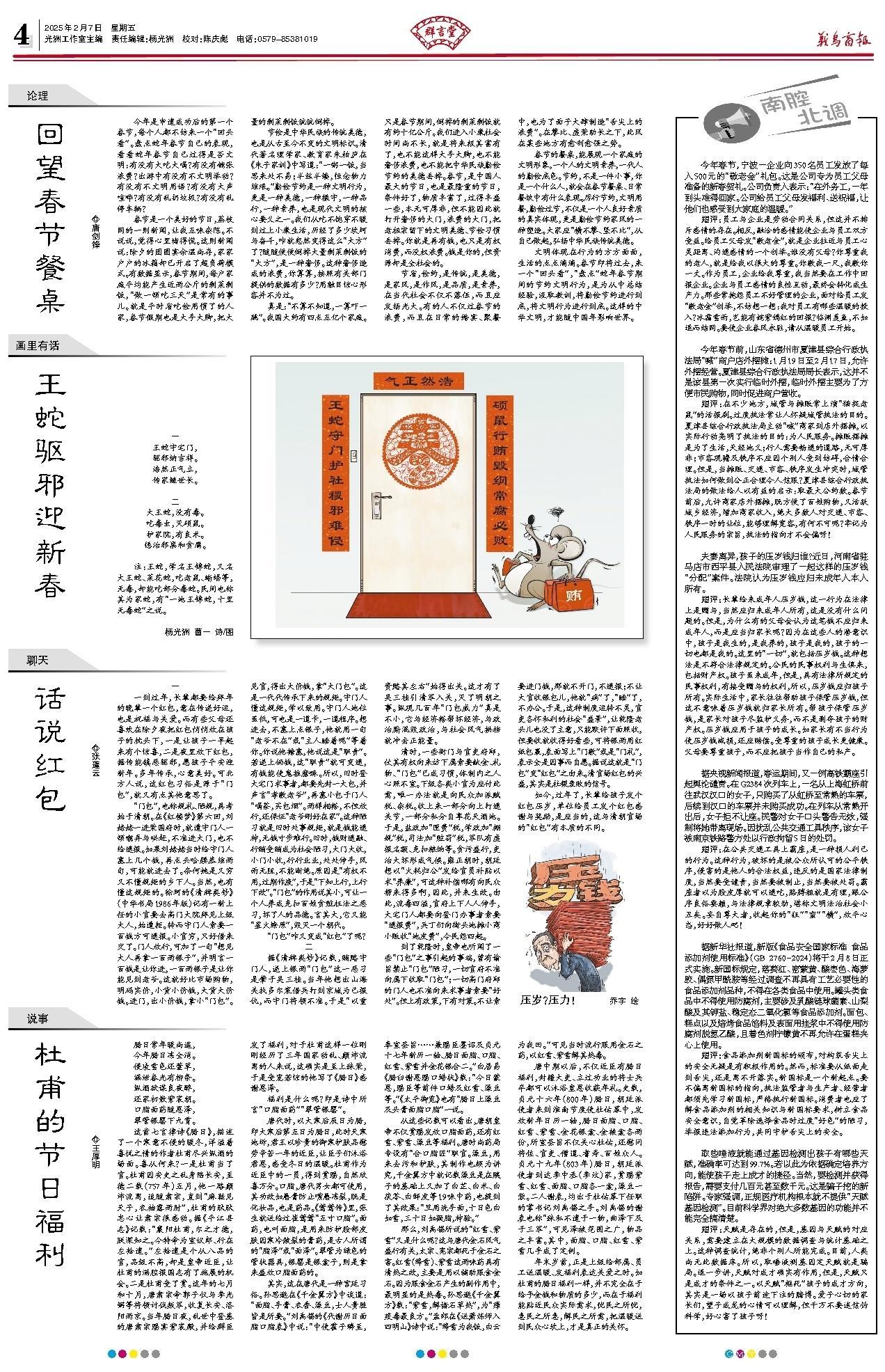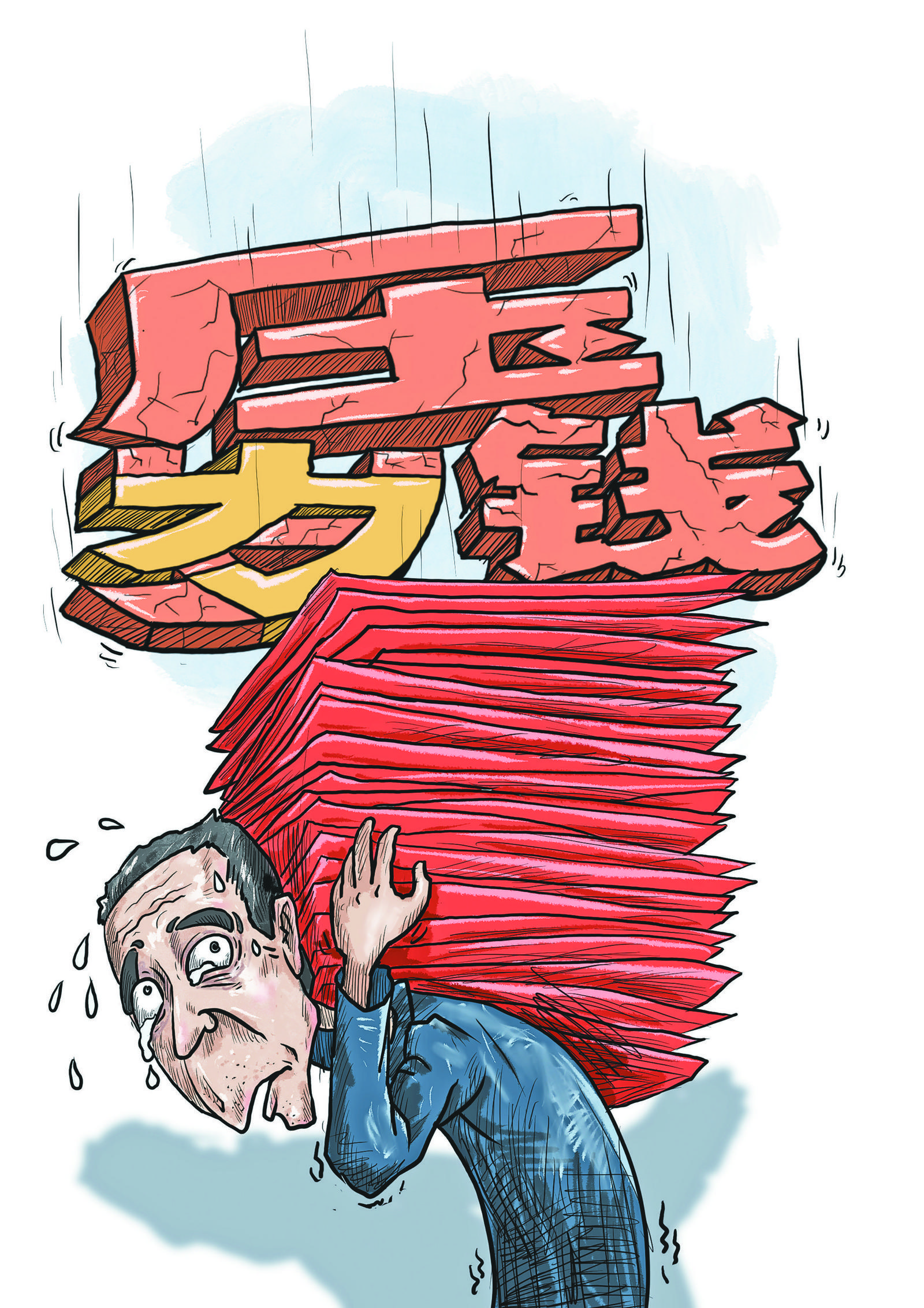一
一到过年,长辈都要给拜年的晚辈一个红包,意在传递好运,也是祝福与关爱。而有些父母还喜欢在除夕夜把红包悄悄放在孩子的枕头下,一是让孩子一早起来有个惊喜,二是夜里放下红包,据传能镇恶驱邪,愿孩子平安迎新年。多年传承,心意美好。可北方人说,这红包习俗是源于“门包”,就又有点其他意思了。
“门包”,也称规礼、陋规,具考始于清朝。在《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就遭守门人一顿嘲弄与哄赶,不准进大门,也不给通报。如果刘姥姥当时给守门人塞上几个钱,再点头哈腰恭维两句,可能就进去了。奈何她是又穷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当然,也有懂这规矩的。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记有一新上任的小官要去高门大院拜见上级大人,始遭拒。转而守门人索要一百钱方可通报。小官穷,只好借来交了。门人放行,可加了一句“想见大人再拿一百两银子”,并明言一百钱是让你进,一百两银子是让你能见到老爷。这就好比市场购物,明码实价,小货小价钱,大货大价钱。进门,出小价钱,拿小“门包”。见官,得出大价钱,拿“大门包”。这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守门人懂这规矩,学以致用。守门人地位虽低,可也是一道卡,一道程序。想进去,不塞上点银子,他就用一句“老爷不在”或“主人睡着呢”等着你。你说他搪塞,他说这是“职责”。若递上俩钱,这“职责”就可变通,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所以,旧时登大宅门求事者,都要先封一大包,并声言“孝敬老爷”,再塞小包于门人“喝茶,买包烟”。两样相搭,不但放行,还保证“老爷刚好在家”。这种陋习就是旧时处事规矩,就是钱能通神,无钱寸步难行。旧时,钱财通融、行贿受贿成为社会陋习,大门大收,小门小收,行行业业,处处伸手,风雨无阻,不能断绝。原因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下知上行,上行下效”。“门包”的作用说其小,可让一个人养成克扣百姓贪赃枉法之恶习,坏了人的品德。言其大,它又能“星火燎原”,毁灭一个朝代。
“门包”咋又变成“红包”了呢?
二
据《清稗类钞》记载,贿赂守门人,递上银两“门包”这一恶习是肇于吴三桂。当年他想出山海关找多尔衮借兵打到京城为己报仇,而守门将领不准。于是“以重资赂其左右”始得出关。这才有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灭了明朝之事。纵观几百年“门包威力”真是不小,它与经济搭帮坏经济,与政治厮混毁政治,与社会风气拱档就冲击正能量。
清时,一些衙门与官吏府邸,仗其有权向来访下属索要献金、礼物、“门包”已成习惯,体制内之人心照不宣。下级各类小官为应付此需,唯一办法就是向民众加派赋税、杂税。收上来一部分向上打通关节,一部分私分自享花天酒地。于是,盐政加“匣费”税,学政加“棚规”税,司法加“赃罚”税,军队有虚报名额、克扣粮饷等。贪污盛行,吏治大坏形成气候。雍正朝时,朝廷想以“火耗归公”发给官员补贴以求“养廉”,可这种补偿哪有向民众捞来得多啊,因此,并未生效。由此,流毒四溢,官府上下人人伸手,大宅门人都要向登门办事者索要“通报费”,兵丁们向街头地摊小商小贩收“地皮费”,令民怨四起。
到了乾隆时,皇帝也听闻了一些“门包”之事引起的事端,曾有谕旨禁止“门包”陋习,一切官府不准向属下收取“门包”;一切高门府邸的门人也不准向来求事者索要“好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让索要进门钱,那就不开门,不通报;不让大官收银包儿,他就“病”了,“睡”了,不办公。于是,这种制度运转不灵,官吏各怀私利的社会“盛景”,让乾隆老头儿也没了主意,只能默许下面照收,但要收就收得好看些,可将银两用红纸包裹,表面写上“门敬”或是“门礼”,表示全是因事而自愿。据说这就是“门包”变“红包”之由来。清官场红包的兴盛,其实是社稷衰败的信号。
如今,过年了,长辈给孩子发个红包压岁,单位给员工发个红包感谢与奖励,是应当的,这与清朝官场的“红包”有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