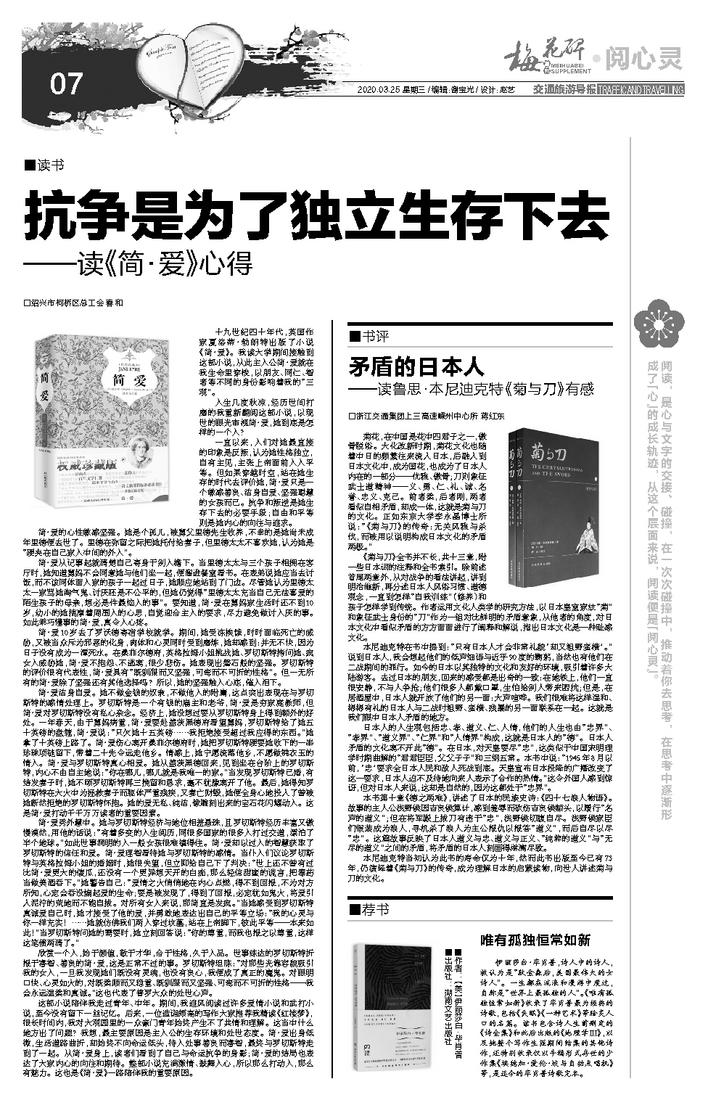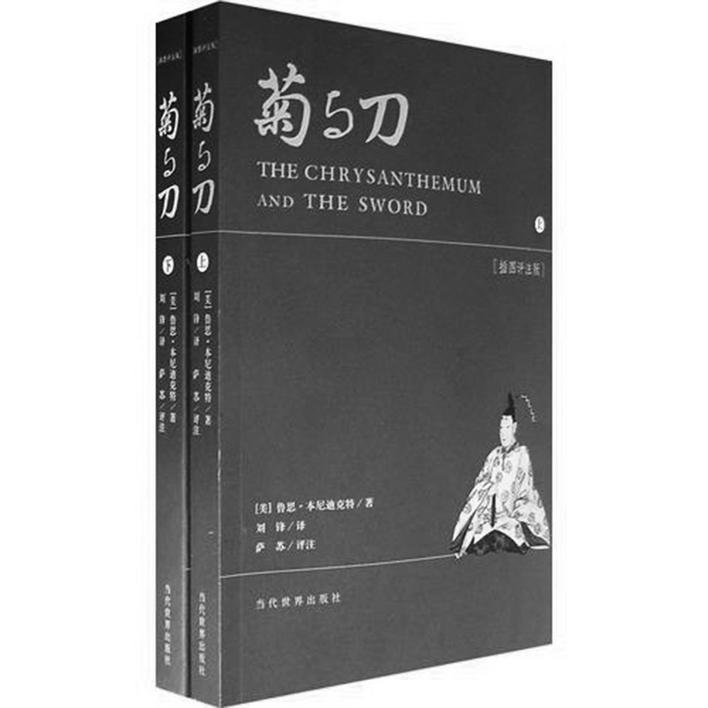菊花,在中国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傲骨脱俗。大化改新时期,菊花文化也随着中日的频繁往来流入日本,后融入到日本文化中,成为国花,也成为了日本人内在的一部分——优雅、傲骨;刀则象征武士道精神——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前者柔,后者刚,两者看似自相矛盾,却成一体,这就是菊与刀的文化。正如东京大学李永晶博士所说:“《菊与刀》的传奇:无关风雅与杀伐,而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的矛盾两极。”
《菊与刀》全书并不长,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到:“只有日本人才会非常礼貌‘却又粗野蛮横’。”说到日本人,我会想起他们的低声细语与近乎90度的鞠躬,当然也有他们在二战期间的罪行。如今的日本以其独特的文化和友好的环境,吸引着许多大陆游客。去过日本的朋友,回来的感受都是出奇的一致:在地铁上,他们一直很安静,不与人争抢;他们很多人都戴口罩,生怕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在居酒屋中,日本人就开放了他们的另一面:大声喧哗。我们很难将这样温和、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与二战时粗野、蛮横、残暴的另一面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眼中日本人矛盾的地方。
日本人的人生观包括忠、孝、道义、仁、人情,他们的人生也由“忠界”、“孝界”、“道义界”、“仁界”和“人情界”构成,这就是日本人的“德”。日本人矛盾的文化离不开此“德”。在日本,对天皇要尽“忠”,这类似于中国宋明理学时期曲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本书中说:“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全日本人民和敌人死战到底。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广播改变了这一要求,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向来人表示了合作的热情。”这令外国人感到惊讶,但对日本人来说,这却是自然的,因为这都处于“忠界”。
本书第十章《德之两难》,讲述了日本的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物语》。故事的主人公浅野侯因吉良侯算计,感到羞辱而砍伤吉良侯额头,以履行“名声的道义”;但在将军殿上拔刀有违于“忠”,浅野侯切腹自尽。浅野侯家臣们假装成为浪人,寻机杀了浪人为主公报仇以报答“道义”,而后自尽以尽“忠”。这篇故事反映了日本人道义与忠、道义与正义、“纯粹的道义”与“无尽的道义”之间的矛盾,将矛盾的日本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此书的寿命仅为十年,然而此书出版至今已有73年,仍演绎着《菊与刀》的传奇,成为理解日本的启蒙读物,向世人讲述菊与刀的文化。
□浙江交通集团上三高速嵊州中心所 蒋红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