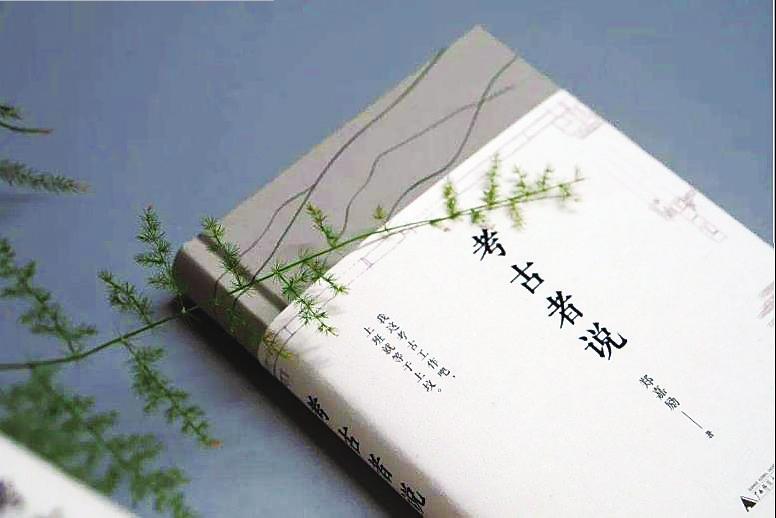一
《考古者说》是考古学家郑嘉励的新著。读完最后一篇《考古人的独白(代后记)》后,我码下最初感受:“执着和专注、毅力和恒心,是择一事、终一生所必需的品质,也是令人钦佩的魅力所在。”
郑嘉励是浙江玉环人,1995年供职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后,“不曾跳槽,更无缘改行”。
我与郑先生素昧平生,但对其文字并不陌生。大约2010年,我在《杭州日报》副刊上读到了他的“考古者说”系列。“田野工作者”是郑嘉励的自我定位,既“非专业作家,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其文学成就也许比不上同版面上的知名作家,却被业界称作“主流学者、小众网红、学术畅销书作家”。后来,他把专栏文稿结集,先后出版了杂文集《考古的另一面》和随笔集《考古四记》。
收录在《考古者说》的文章,被剖为“寻墓”“语石”“读城”“格物”4辑。郑嘉励犹如一位烹饪大师,以古代物事为食材,灵活运用中华料理十八般技巧,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一一整合起来,烩就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读之,不免让人感到:考古原来这么有意思!
刨地、开墓、棺木、厉鬼、太平间、火葬场……大凡与死亡有牵连的事物或意象,考古工作者几乎天天都要碰到。说“有意思”,其实是假的。之所以让人产生“错觉”,盖因郑嘉励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妙语连珠。
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古工作,不能只挖土,还得会读书。郑嘉励每到一个新地方,便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他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
“属地管理”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特质,郑嘉励足迹又局限于浙江范围——“偏安一隅”,难免影响拳脚施展。但是,“读书”,让郑嘉励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又确保他将一个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皆落脚于人文关照,感性的表达和富有情趣的笔法让人耳目一新。
“上班就是上坟”,是郑嘉励先生的名言,亦是网络热词。在《考古者说》中,郑先生以它开篇,用意显而易见。因为这话虽“略带自嘲之意,整体而言,还算是对工作的客观描述。”
按旧时说法,凡是无人收葬、祭祀的亡魂,都会变成到处作祟的厉鬼。于是,热心建造“义冢”,便成为古代城乡常见的慈善行为。
有一次,郑嘉励到义乌赤岸,还见过“厉鬼坛”,那是过去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他说:“建造义冢的好心人,对孤魂野鬼心存善念、敬畏,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敬爱与畏惧,这两种不同的情绪,容易混为一谈。古人收殓陌生人的骨殖,一半因为敬重,一半因为恐惧。好比苍天在上,我们也很难说自己是敬重大自然呢,还是因为害怕大自然;又好比我们坐在台下,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讲话,皆作洗耳恭听状,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还是因为怕他?”(《义冢》)
听出来了吧,郑嘉励的文字借古讽今,有大先生的遗风。
三
古婺,“浙江之心”——2200年,是历史长度;万年上山,乃文脉厚度。较之于其它地市,郑先生对金华是偏爱的,“说”得多,分量也最重。
武义不大,但文脉悠长,是郑先生频频光顾的重要“考点”。徐谓礼文书是武义博物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想当年,盗墓贼得手后,销赃者认定鲜美如昨的文书为“赝品”。郑嘉励慧眼识宝,终于促成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案情扑朔迷离,文书失而复得。每次前往参观,听人讲解文书内容,不仅简明易懂,而且引人入胜,有一种与众不同之感。
2019年4月,郑嘉励应武义博物馆邀请,领着讲解员在展厅转了一圈,针对众人疑问,一一作了解答。一篇涉及南宋政治、官制、文书、墓葬制度的解说词便水到渠成。郑嘉励说:“最好的讲解,是口语的,是闲聊的,是生活的,是不着痕迹的精心准备。”
近年来,郑嘉励扎根金华古子城的几个“点”,又兼顾老城区的整个“面”,带着问题,走透了每一个角度、每一处古迹,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得的《金华四记》。
不过,如果说武义是郑嘉励先生的“福地”,那么,金华古城无疑令他“揪心”。城墙的四至,即老城区的边界,曾为城市最直观的象征。金华旧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以后,还记得古子城城墙现在何处?而今,哪里去寻和吕祖谦相关的一览亭、吕成公祠、丽泽书院等遗迹?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郑嘉励是专家型学者,“四记”中的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给金华人留足了面子。郑嘉励说:“时代发展太快,又有人主张放慢脚步……呼吁重建金华府衙、府学。然而,事过境迁,重建的‘古迹’也不过是昨日蜕变后留下的躯壳,历史已永远无法重来。”
诚哉斯言!
□潘江涛
(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