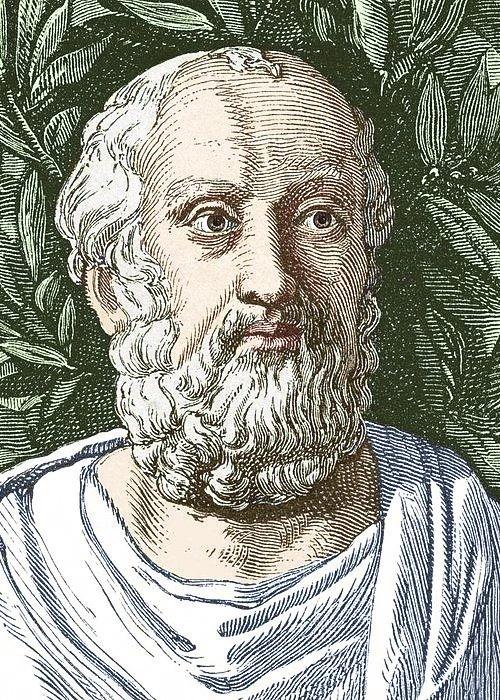无论对一个故事的理解有多不同,只要能够从中得到思考,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倾听。今天,我想就众说纷纭的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故事,谈谈我的现代诗写作从中得到的关于“人之善”的启示。限于篇幅,我仅从文学角度加以简述。
雅典德尔菲神庙里有一道神谕,说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但苏格拉底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于是他四处探访,逢人就提问,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据说,苏格拉底向只是提问,从不给出最终答案,即当对方说出自己的答案时,他总是进一步追问答案的源头。比如他问:什么是美?对方答:你看那边那个姑娘,她很美。苏格拉底对这样的答案很不满意,进一步追问:我问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那个姑娘。也就说,苏格拉底式提问,其实是在“逼迫”对方进行“反思”。被他提问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后,感到恼羞成怒者不在少数。这些恼羞成怒者认为苏格拉底在让他出丑,在无理取闹。苏格拉底的这种提问方式,目的并非要让对方赞同他的见解(他本人也没有答案),而是一种寻求真理的方法,让每个人最终认识自己、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最终,雅典法庭以“污染年轻人的思想罪”而判他死刑。当然,我更相信这是一个文学的隐喻。
真实的背景是,经过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统治者对自身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十分敏感。其次是苏格拉底提问的方式,他自己并不提出什么观点,而是从对方的观点中寻找漏洞,迫使对方自行完善他的理论,是一种哲思式提问。可以说,苏格拉底的诘问,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种要求其反思自我式的提问。这对受战争强权影响的人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人们在这种时候更加看重财富与权力,对所谓的反省、智慧并不感兴趣。因为苏格拉底的自我反省式提问,其实就是自我否定,对应于现实世界,就是一种消亡。
所以,从现实这一层来讲,苏格拉底被提起公诉被判死刑,是他的时代命运。
苏格拉底被关进监狱之后,他还有机会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一个学生买通狱卒,让他越狱,但他拒绝了。甚至,在监狱赐他毒药自尽时,当他知道给他的一碗草药刚刚够毒死他的药量,他竟打消了“将毒药撒一点在地上敬神”的想法,一饮而尽。之后,苏格拉底上半身出现中毒情况,不能动,然后全身才僵硬。整个过程,狱卒对他十分礼貌,他的亲人和学生也都在身边。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自己选择了死亡。
苏格拉底为什么自愿去死呢?这里涉及到一个“人之善”的问题。我这里讲的“善”并非狭义的善良,而是广义上的人之善——人的行为是为了弥补人的缺陷的一种存在。这里的人也非指个人,而是指所有人及人这个物种。雅典法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代表了人的一个意志。苏格拉底参与了这个法律的制定,也就是说,他死于自己的意志,也即死于人的意志。苏格拉底难道不知道审判他的法官有罪吗?当然知道。但他已经将这种罪恶理解为“人之罪”,而非个人之罪。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来表达:人必须为自己的罪恶而受到惩罚,如此,人才能生活得更好。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为他翻案,为他雕刻了塑像。人们意识到雅典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智者。
指控和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有罪,这个“罪”是人的一种恶,是人的一个自我本性。从这个角度讲,这种罪本身是人的一种缺陷,是不完善。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唤醒人类意识到人的这种有限性,并希望用自己的死弥补人的这种缺陷。苏格拉底之死,本质上也是他对“我知我无知”的哲学践行。
这个故事对现代诗的启示是:现代诗应当秉承这种“苏格拉底的善意”,为了人,为了人类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更好地活下去。苏格拉底为人这个物种之“恶”(不完善)而愿承担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利益甚至死亡之上的“人”的救赎。我所理解的现代诗的本质,就是反思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是这种反思,让我们不断对自身的缺陷加以纠正和补充,使人不断走向那个完善的“人”。
□麦豆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