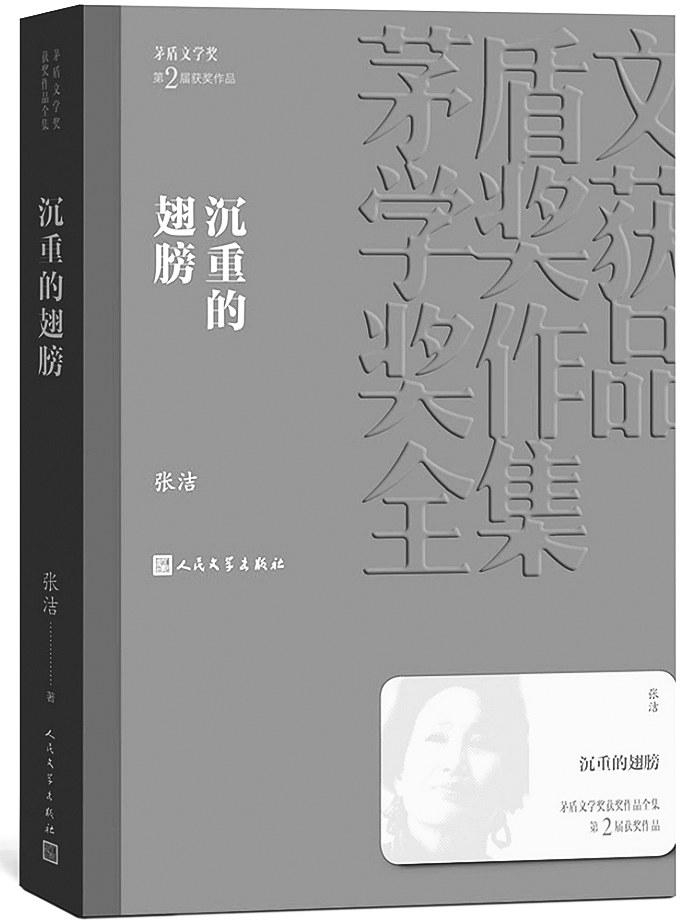女作家张洁今年1月份在美国去世,我从未见过真人,也未曾听过她的婚恋传闻,其容貌也是这几天在网上才看见。
为什么想着致谢她,是因为我在上游造船厂的铸造车间上班时,偶读了刊登在《十月》1981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者张洁极力推崇“行为科学”,在她编的故事中说道:
“H大学的陈校长,是中国工业心理学专家。这个学校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这位校长七十多岁了,亲自出马,带着教师和研究生,到工厂做调查研究。工业心理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前些年,心理学被打倒了,现在逐步恢复。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只有H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陈校长是英国留学学工业心理学的。”
后在福建省高招办逐页翻阅198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目录时,顿时联想到她小说中所提及的H大学即是杭州大学;留学英国的“陈校长”,即是因素分析之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E.Spear⁃man)的弟子-陈立教授。猜中了张洁布下的字谜,心中窃喜。当年全国仅有4所大学设有心理学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在这4个备择项中我选择了考H大学工业心理学。闷头连续考研3年,屡败屡战,终在85年戴上了“桔红色的校徽”,可以不必藏着掖着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她不经意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的走向。在那个年代,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从工科投向“工业心理学”。多年后,我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原系主任孙健敏,在1985年也报考了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的研究生。论本科专业,他比我强(高端),他念的是锻造(Forging),我念的是铸造(Casting)。
我想,不仅我要感谢张洁,杭州大学心理学(现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以及研究“行为科学”的人都要感谢她。抑或是该小说叙述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的原型是孙友余的缘故,当时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孙友余对“行为科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我考入杭州大学的1985年,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在北京成立,会长即是孙友余副部长。1999年陈立先生撰文如是说:
“过去因孙友余同志的倡导,行为科学曾在中国80年代盛极一时,对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都作出了许多成绩,并且成立了全国的行为科学学会,办了几期厂长经理的培训班,为我国的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成为一种推动作用。后孙友余同志因病离职,行为科学学会名存实亡,现在已无全国的学会组织。”
至今,机械工业出版社仍然是出版心理学书籍的重镇。比如它出版的奚恺元作品《别做正常的傻瓜》。
我心底清楚,张洁走了,她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她的文字竟能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借用一个反方向的例子类比,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里,一句轻描淡写的“假项链”,害惨了女主人玛蒂尔德,用自己的10年青春还完了不该偿还的债务。屈指数来,自从我1985年进入工业心理学领域,一直忙到现在退休,因为有了我的入行,中科院心理所的行为决策课题组曾经先后聚集80多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
这就是小说作家张洁自己不曾想到的“扇力”。
也因为小说里的一句话,我一直相信,追本溯源我国的工业心理学当是陈立先生于1930年师从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然而,直到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陈立先生并不是最早跟从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的中国人。知道真相,我似乎比《项链》女主人多花了30年时间。
一次我访问聊城大学心理系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带领我参观了傅斯年陈列馆(傅氏祠堂)。在聊城大学的校园里,立着傅斯年的塑像,他家乡的人民以他是“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为荣。
在观看展品时,我蓦然发现,学霸傅斯年竟在1920年就受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权威心理学学者斯皮尔曼,比陈立先生早了整整10年。而且,他在中山大学讲授的正是斯皮尔曼的真经。
在核实了当地心理学者都不知晓的傅斯年与心理学的关系之后,我便怂恿年轻教师用傅斯年很奇怪的英文名-FuSsu-nien作为作者名去查找更多的外文资料,去申请地方的社科基金,去将研究傅斯年的成果发表在心理学而非语言历史类的学术期刊上。
果然,数年后,这些个“不经意”的事竟都成了。年轻老师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傅斯年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人关系密切,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事成,我觉得我会比聊城大学的年轻教师更欢喜。以小人之心度之,我想张洁及喜欢她的读者群或许会很受用。因为,她不经意扇了一下翅膀,就扇出了改变别人命运的蝴蝶效应,也让活着的人就此明白:人的一生,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李纾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中国侨联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