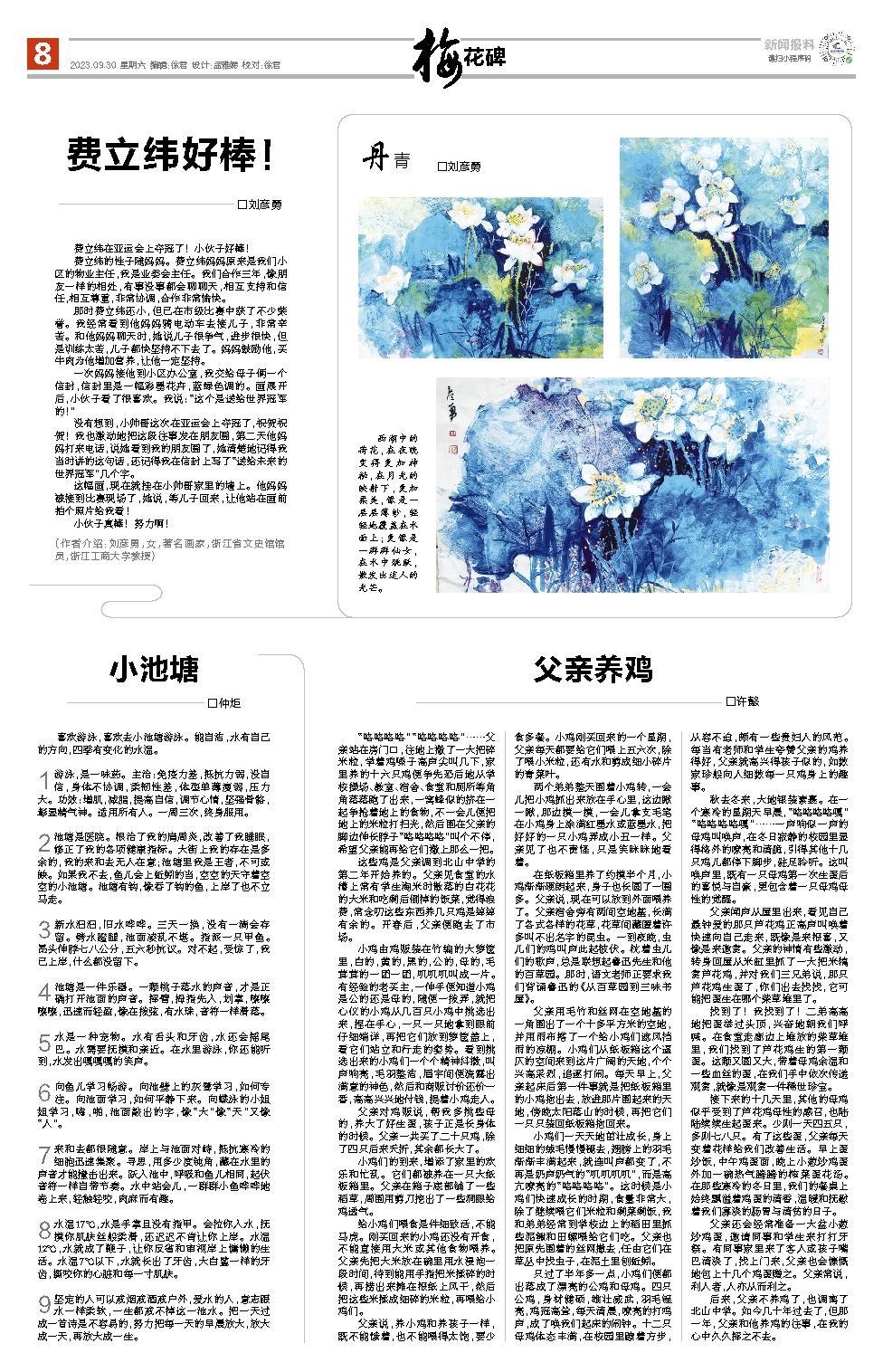“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父亲站在房门口,往地上撒了一大把碎米粒,学着鸡嗓子高声尖叫几下,家里养的十六只鸡便争先恐后地从学校操场、教室、宿舍、食堂和厕所等角角落落跑了出来,一窝蜂似的挤在一起争抢着地上的食物,不一会儿便把地上的米粒打扫光,然后围在父亲的脚边伸长脖子“咯咯咯咯”叫个不停,希望父亲能再给它们撒上那么一把。
这些鸡是父亲调到北山中学的第二年开始养的。父亲见食堂的水槽上常有学生淘米时散落的白花花的大米和吃剩后倒掉的饭菜,觉得浪费,常念叨这些东西养几只鸡是绰绰有余的。开春后,父亲便跑去了市场。
小鸡由鸡贩装在竹编的大箩筐里,白的,黄的,黑的,公的,母的,毛茸茸的一团一团,叽叽叽叫成一片。有经验的老买主,一伸手便知道小鸡是公的还是母的,随便一拨弄,就把心仪的小鸡从几百只小鸡中挑选出来,捏在手心,一只一只地拿到眼前仔细端详,再把它们放到箩筐盖上,看它们站立和行走的姿势。看到挑选出来的小鸡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叫声响亮,毛羽整洁,眉宇间便流露出满意的神色,然后和商贩讨价还价一番,高高兴兴地付钱,提着小鸡走人。
父亲对鸡贩说,帮我多挑些母的,养大了好生蛋,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父亲一共买了二十只鸡,除了四只后来夭折,其余都长大了。
小鸡们的到来,增添了家里的欢乐和忙乱。它们都被养在一只大纸板箱里。父亲在箱子底部铺了一些稻草,周围用剪刀挖出了一些洞眼给鸡透气。
给小鸡们喂食是件细致活,不能马虎。刚买回来的小鸡还没有开食,不能直接用大米或其他食物喂养。父亲先把大米放在碗里用水浸泡一段时间,待到能用手指把米揉碎的时候,再捞出来摊在报纸上风干,然后把这些米揉成细碎的米粒,再喂给小鸡们。
父亲说,养小鸡和养孩子一样,既不能饿着,也不能喂得太饱,要少食多餐。小鸡刚买回来的一个星期,父亲每天都要给它们喂上五六次,除了喂小米粒,还有水和剪成细小碎片的青菜叶。
两个弟弟整天围着小鸡转,一会儿把小鸡抓出来放在手心里,这边瞅一瞅,那边摸一摸,一会儿拿支毛笔在小鸡身上涂满红墨水或蓝墨水,把好好的一只小鸡弄成小丑一样。父亲见了也不责怪,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在纸板箱里养了约摸半个月,小鸡渐渐硬朗起来,身子也长圆了一圈多。父亲说,现在可以放到外面喂养了。父亲宿舍旁有两间空地基,长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花草间藏匿着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昆虫。一到夜晚,虫儿们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枕着虫儿们的歌声,总是联想起鲁迅先生和他的百草园。那时,语文老师正要求我们背诵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用毛竹和丝网在空地基的一角围出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空地,并用雨布搭了一个给小鸡们遮风挡雨的凉棚。小鸡们从纸板箱这个逼仄的空间来到这片广阔的天地,个个兴高采烈,追逐打闹。每天早上,父亲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纸板箱里的小鸡抱出去,放进那片围起来的天地,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再把它们一只只装回纸板箱抱回来。
小鸡们一天天地茁壮成长,身上细细的绒毛慢慢褪去,翅膀上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就连叫声都变了,不再是奶声奶气的“叽叽叽叽”,而是高亢嘹亮的“咯咯咯咯”。这时候是小鸡们快速成长的时期,食量非常大,除了继续喂它们米粒和剩菜剩饭,我和弟弟经常到学校边上的稻田里抓些泥鳅和田螺喂给它们吃。父亲也把原先围着的丝网撤去,任由它们在草丛中找虫子,在泥土里刨蚯蚓。
只过了半年多一点,小鸡们便都出落成了漂亮的公鸡和母鸡。四只公鸡,身材健硕,雄壮威武,羽毛锃亮,鸡冠高耸,每天清晨,嘹亮的打鸣声,成了唤我们起床的闹钟。十二只母鸡体态丰满,在校园里踱着方步,从容不迫,颇有一些贵妇人的风范。每当有老师和学生夸赞父亲的鸡养得好,父亲就高兴得孩子似的,如数家珍般向人细数每一只鸡身上的趣事。
秋去冬来,大地银装素裹。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咯咯咯咯嘎”“咯咯咯咯嘎”……一声响似一声的母鸡叫唤声,在冬日寂静的校园里显得格外的嘹亮和清脆,引得其他十几只鸡儿都停下脚步,驻足聆听。这叫唤声里,既有一只母鸡第一次生蛋后的喜悦与自豪,更包含着一只母鸡母性的觉醒。
父亲闻声从屋里出来,看见自己最钟爱的那只芦花鸡正高声叫唤着快速向自己走来,既像是来报喜,又像是来邀赏。父亲的神情有些激动,转身回屋从米缸里抓了一大把米犒赏芦花鸡,并对我们三兄弟说,那只芦花鸡生蛋了,你们出去找找,它可能把蛋生在哪个柴草堆里了。
找到了!我找到了!二弟高高地把蛋举过头顶,兴奋地朝我们呼喊。在食堂走廊边上堆放的柴草堆里,我们找到了芦花鸡生的第一颗蛋。这颗又圆又大,带着母鸡余温和一些血丝的蛋,在我们手中依次传递观赏,就像是观赏一件稀世珍宝。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其他的母鸡似乎受到了芦花鸡母性的感召,也陆陆续续生起蛋来。少则一天四五只,多则七八只。有了这些蛋,父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改善生活。早上蛋炒饭,中午鸡蛋面,晚上小葱炒鸡蛋外加一碗热气腾腾的榨菜蛋花汤。在那些寒冷的冬日里,我们的餐桌上始终飘溢着鸡蛋的清香,温暖和抚慰着我们寡淡的肠胃与清贫的日子。
父亲还会经常准备一大盆小葱炒鸡蛋,邀请同事和学生来打打牙祭。有同事家里来了客人或孩子嘴巴清淡了,找上门来,父亲也会慷慨地包上十几个鸡蛋赠之。父亲常说,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后来,父亲不养鸡了,也调离了北山中学。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那一年,父亲和他养鸡的往事,在我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许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