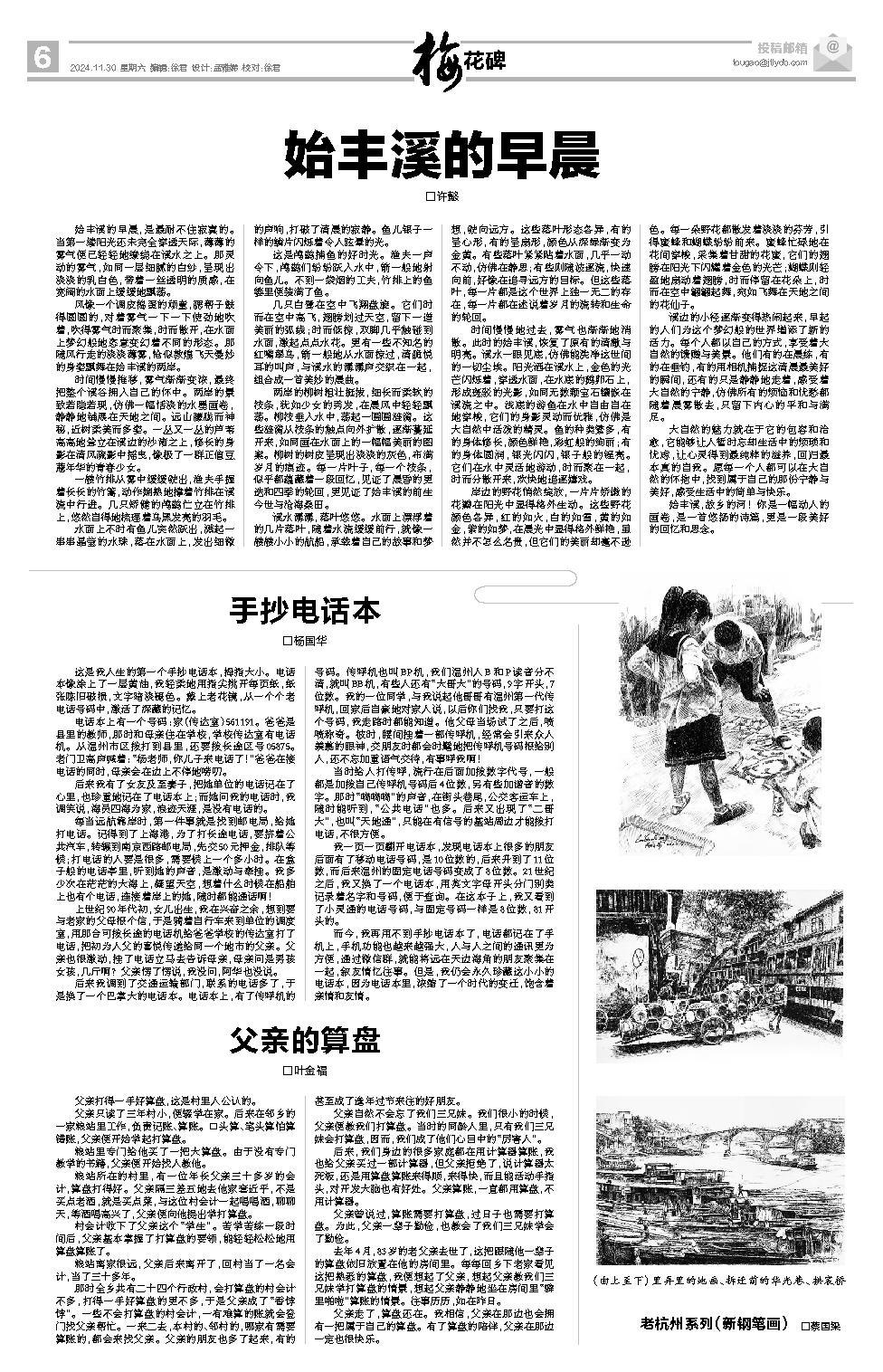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手抄电话本,拇指大小。电话本像涂上了一层黄油,我轻柔地用指尖挑开每页纸,纸张陈旧破损,文字暗淡褪色。戴上老花镜,从一个个老电话号码中,激活了深藏的记忆。
电话本上有一个号码:家(传达室)561191。爸爸是县里的教师,那时和母亲住在学校,学校传达室有电话机。从温州市区拨打到县里,还要拨长途区号05875。老门卫高声喊着:“杨老师,你儿子来电话了!”爸爸在接电话的同时,母亲会在边上不停地唠叨。
后来我有了女友及至妻子,把她单位的电话记在了心里,也珍重地记在了电话本上;而她问我的电话时,我调笑说,海员四海为家,浪迹天涯,是没有电话的。
每当远航靠岸时,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邮电局,给她打电话。记得到了上海港,为了打长途电话,要挤着公共汽车,转辗到南京西路邮电局,先交50元押金,排队等候;打电话的人要是很多,需要候上一个多小时。在盒子般的电话亭里,听到她的声音,是激动与牵挂。我多少次在茫茫的大海上,凝望天空,想着什么时候在船舶上也有个电话,连接着岸上的她,随时都能通话啊!
上世纪90年代初,女儿出生,我在兴奋之余,想到要与老家的父母报个信,于是骑着自行车来到单位的调度室,用那台可拨长途的电话机给爸爸学校的传达室打了电话,把初为人父的喜悦传递给同一个地市的父亲。父亲也很激动,挂了电话立马去告诉母亲,母亲问是男孩女孩,几斤啊?父亲愣了愣说,我没问,阿华也没说。
后来我调到了交通运输部门,联系的电话多了,于是换了一个巴掌大的电话本。电话本上,有了传呼机的号码。传呼机也叫BP机,我们温州人B和P读音分不清,就叫BB机,有些人还有“大哥大”的号码,9字开头,7位数。我的一位同学,与我说起他哥哥有温州第一代传呼机,回家后自豪地对家人说,以后你们找我,只要打这个号码,我走路时都能知道。他父母当场试了之后,啧啧称奇。彼时,腰间挂着一部传呼机,经常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眼神,交朋友时都会时髦地把传呼机号码报给别人,还不忘加重语气交待,有事呼我啊!
当时给人打传呼,流行在后面加拨数字代号,一般都是加拨自己传呼机号码后4位数,另有些加谐音的数字。那时“嘀嘀嘀”的声音,在街头巷尾,公交客运车上,随时能听到,“公共电话”也多。后来又出现了“二哥大”,也叫“天地通”,只能在有信号的基站周边才能拨打电话,不很方便。
我一页一页翻开电话本,发现电话本上很多的朋友后面有了移动电话号码,是10位数的,后来升到了11位数,而后来温州的固定电话号码变成了8位数。21世纪之后,我又换了一个电话本,用英文字母开头分门别类记录着名字和号码,便于查询。在这本子上,我又看到了小灵通的电话号码,与固定号码一样是8位数,81开头的。
而今,我再用不到手抄电话本了,电话都记在了手机上,手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人与人之间的通讯更为方便,通过微信群,就能将远在天边海角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叙友情忆往事。但是,我仍会永久珍藏这小小的电话本,因为电话本里,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变迁,饱含着亲情和友情。
□杨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