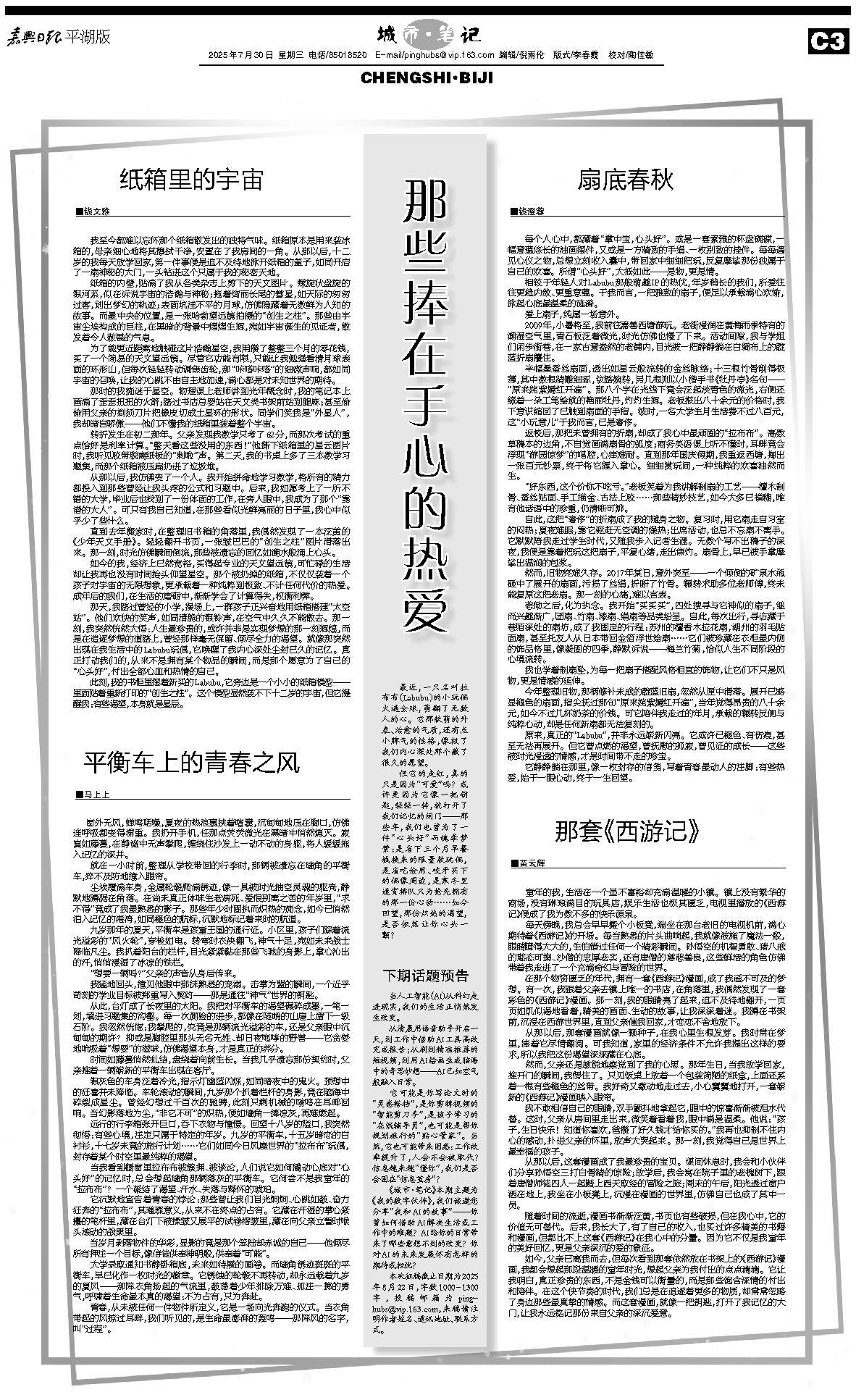■马上上
窗外无风,蝉鸣聒噪,夏夜的热浪裹挟着喧嚣,沉甸甸地压在胸口,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滞重。我扔开手机,任那点荧荧微光在黑暗中悄然熄灭。寂寞如藤蔓,在静谧中无声攀爬,缠绕住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身躯,将人缓缓拖入记忆的深井。
就在一小时前,整理从学校带回的行李时,那辆被遗忘在墙角的平衡车,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
尘埃覆满车身,金属轮毂爬满锈迹,像一具被时光抽空灵魂的躯壳,静默地蹲踞在角落。在尚未真正体味生老病死、爱恨别离之苦的年岁里,“求不得”竟成了我最熟悉的影子。那些年少时固执而炽热的痴念,如今已悄然泊入记忆的港湾,如同褪色的航标,沉默地标记着来时的航道。
九岁那年的夏天,平衡车是孩童王国的通行证。小区里,孩子们踩着流光溢彩的“风火轮”,穿梭如电。转弯时衣袂翻飞,神气十足,宛如未来战士降临凡尘。我扒着阳台的栏杆,目光紧紧黏在那些飞驰的身影上,掌心沁出的汗,悄悄浸湿了冰凉的铁栏。
“想要一辆吗?”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猛地回头,撞见他眼中那抹熟悉的宠溺。击掌为盟的瞬间,一个近乎苛刻的学业目标被郑重写入契约——那是通往“神气”世界的钥匙。
从此,台灯成了长夜里的太阳。我把对平衡车的渴望碾碎成墨,一笔一划,填进习题集的沟壑。每一次测验的进步,都像在陡峭的山崖上凿下一级石阶。我忽然恍惚:我攀爬的,究竟是那辆流光溢彩的车,还是父亲眼中沉甸甸的期许?抑或是胸腔里那头无名无姓、却日夜咆哮的野兽——它贪婪地吮吸着“想要”的滋味,仿佛渴望本身,才是真正的养分。
时间如藤蔓悄然虬结,盘绕着向前生长。当我几乎遗忘那份契约时,父亲推着一辆崭新的平衡车出现在客厅。
银灰色的车身泛着冷光,指示灯幽蓝闪烁,如同暗夜中的鬼火。预想中的狂喜并未降临。车轮滚动的瞬间,九岁那个扒着栏杆的身影,竟在脑海中碎裂成星尘。曾经幻想过千百次的驰骋,此刻只剩机械的嗡鸣在耳畔回响。当幻影落地为尘,“非它不可”的炽热,便如墙角一捧凉灰,再难燃起。
远行的行李箱张开巨口,吞下衣物与憧憬。回望十八岁的隘口,我突然彻悟:有些心境,注定只属于特定的年岁。九岁的平衡车,十五岁暗恋的白衬衫,十七岁未竟的旅行计划……它们如同今日风靡世界的“拉布布”玩偶,封存着某个时空里最纯粹的渴望。
当我看到橱窗里拉布布被簇拥、被谈论,人们说它如何撬动心底对“心头好”的记忆时,总会想起墙角那辆落灰的平衡车。它何尝不是我童年的“拉布布”?一个凝结了渴望、汗水、失落与释怀的琥珀。
它沉默地宣告着青春的悖论:那些曾让我们目光炯炯、心跳如鼓、奋力狂奔的“拉布布”,其璀璨意义,从来不在终点的占有。它藏在汗湿的掌心紧攥的笔杆里,藏在台灯下被揉皱又展平的试卷褶皱里,藏在向父亲立誓时喉头滚动的战栗里。
当岁月剥落物件的华彩,显影的竟是那个笨拙却赤诚的自己——他倾尽所有押注一个目标,像信徒供奉神明般,供奉着“可能”。
大学录取通知书静卧箱底,未来如待展的画卷。而墙角锈迹斑斑的平衡车,早已化作一枚时光的徽章。它锈蚀的轮毂不再转动,却永远载着九岁的夏风——那阵衣角扬起的气流里,鼓荡着少年排除万难、孤注一掷的勇气,呼啸着生命最本真的渴望:不为占有,只为奔赴。
青春,从未被任何一件物件所定义,它是一场向光奔跑的仪式。当衣角带起的风掠过耳畔,我们听见的,是生命最澎湃的轰鸣——那阵风的名字,叫“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