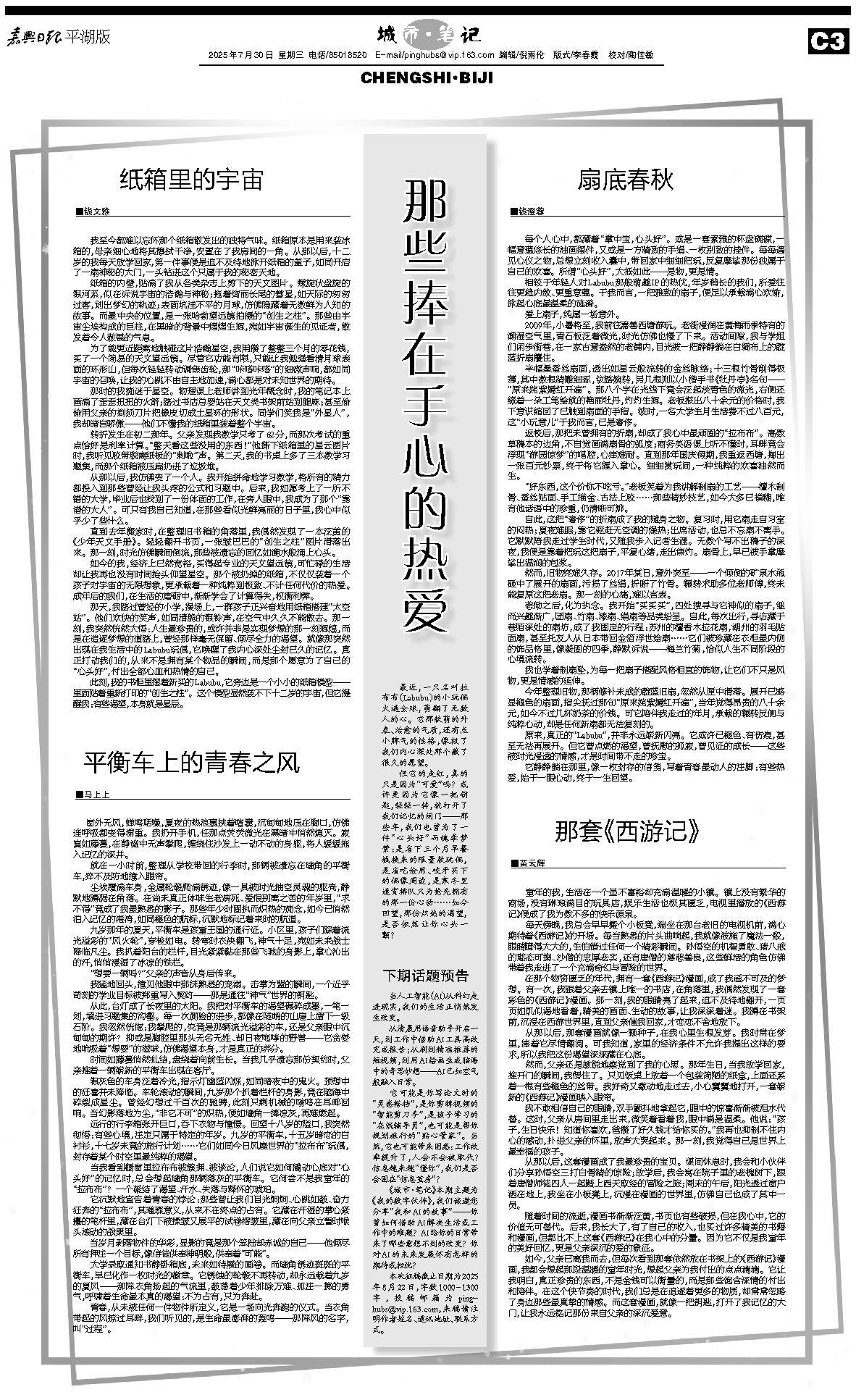■钱澄蓉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掌中宝,心头好”。或是一套素雅的杯盘碗碟,一幅意蕴悠长的油画摆件,又或是一方精致的手绢、一枚别致的挂件。每每遇见心仪之物,总想立刻收入囊中,带回家中细细把玩,反复摩挲那份独属于自己的欢喜。所谓“心头好”,大抵如此——是物,更是情。
相较于年轻人对Labubu那般萌趣IP的热忱,年岁稍长的我们,所爱往往更趋内敛、更重意蕴。于我而言,一把雅致的扇子,便足以承载满心欢愉,掀起心底最温柔的涟漪。
爱上扇子,纯属一场意外。
2009年,小暑将至,我前往嘉善西塘游玩。老街浸润在黄梅雨季特有的潮湿空气里,青石板泛着微光,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活动间隙,我与学姐们闲步街巷,在一家古意盎然的老铺内,目光被一把静静躺在白绸布上的靛蓝折扇攫住。
半幅桑蚕丝扇面,透出如星云般流转的金丝脉络;十三根竹骨削得极薄,其中数根精雕细琢,纹路婉转,另几根则以小楷手书《牡丹亭》名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八个字在光线下竟会泛起淡青色的微光,右侧还缀着一朵工笔绘就的艳丽牡丹,灼灼生辉。老板报出八十余元的价格时,我下意识缩回了已触到扇面的手指。彼时,一名大学生月生活费不过八百元,这“小玩意儿”于我而言,已是奢侈。
返校后,那把未曾拥有的折扇,却成了我心中最顽固的“拉布布”。高数草稿本的边角,不自觉画满扇骨的弧度;商务英语课上听不懂时,耳畔竟会浮现“游园惊梦”的唱腔,心痒难耐。直到那年国庆假期,我重返西塘,掏出一张百元钞票,终于将它握入掌心。细细赏玩间,一种纯粹的欢喜油然而生。
“好东西,这个价你不吃亏。”老板笑着为我讲解制扇的工艺——檀木制骨、蚕丝贴面、手工描金、古法上胶……那些精妙技艺,如今大多已模糊,唯有他话语中的珍重,仍清晰可辨。
自此,这把“奢侈”的折扇成了我的随身之物。复习时,用它扇走自习室的闷热;夏夜难眠,靠它驱赶无空调的燥热;出席活动,也总不忘扇不离手。它默默陪我走过学生时代,又随我步入记者生涯。无数个写不出稿子的深夜,我便是靠着把玩这把扇子,平复心绪,走出焦灼。扇骨上,早已被手掌摩挲出温润的包浆。
然而,旧物终难久存。2017年某日,意外突至——一个倾倒的矿泉水瓶砸中了展开的扇面,污损了丝绢,折断了竹骨。辗转求助多位老师傅,终未能复原这把老扇。那一刻的心痛,难以言表。
悲恸之后,化为执念。我开始“买买买”,四处搜寻与它神似的扇子,继而兴趣渐广,团扇、竹扇、漆扇、绢扇等品类纷呈。自此,每次出行,寻访藏于巷陌深处的扇坊,成了我固定的行程:苏州的檀香木拉花扇,湖州的羽毛贴面扇,甚至托友人从日本带回金箔浮世绘扇……它们被珍藏在衣柜最内侧的饰品格里,像凝固的四季,静默诉说——梅兰竹菊,恰似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流转。
我也学着制扇坠,为每一把扇子搭配风格相宜的饰物,让它们不只是风物,更是情感的延伸。
今年整理旧物,那柄修补未成的靛蓝旧扇,忽然从匣中滑落。展开已略显褪色的扇面,指尖抚过那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当年觉得昂贵的八十余元,如今不过几杯奶茶的价钱。可它陪伴我走过的年月,承载的辗转反侧与纯粹心动,却是任何新扇都无法复刻的。
原来,真正的“Labubu”,并非永远崭新闪亮。它或许已褪色、有伤痕,甚至无法再展开。但它曾点燃的渴望,曾抚慰的孤寂,曾见证的成长——这些被时光浸透的情感,才是时间带不走的珍宝。
它静静躺在那里,像一枚封存的信笺,写着青春最动人的注脚:有些热爱,始于一眼心动,终于一生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