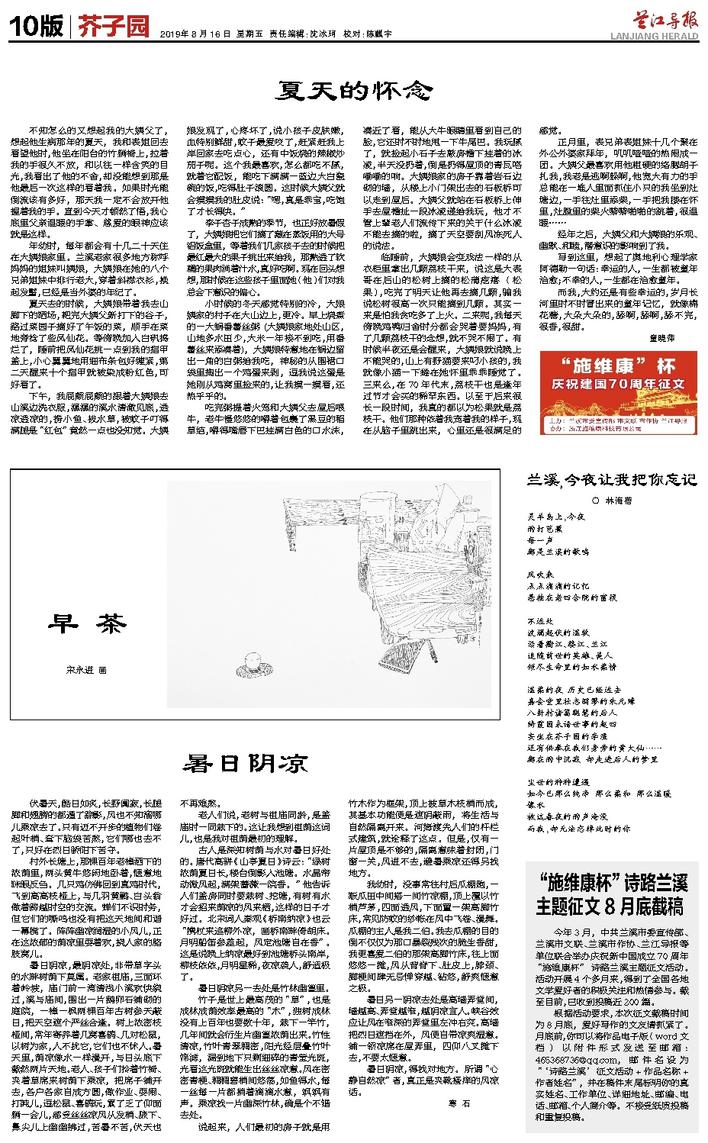暑日阴凉
伏暑天,酷日如炙,长野阒寂,长腿脚和翅膀的都遁了踪影,风也不知溜哪儿乘凉去了。只有迈不开步的植物们卷起叶梢、耷下脑袋苦熬,它们哪也去不了,只好在烈日骄阳下苦守。
村外长塘上,那棵百年老樟洒下的浓荫里,两头黄牛悠闲地卧着,惬意地眯眼反刍。几只鸡仿佛回到真鸡时代,飞到高高枝桠上,与几羽黄鹂、白头翁做着跨越时空的交流。蝉们不识时务,但它们的嘶鸣也没有把这天地间和谐一幕搅了。阵阵幽凉润湿的小风儿,正在这浓郁的荫凉里耍着欢,挠人家的胳肢窝儿。
暑日阴凉,最阴凉处,非带草字头的水畔树荫下莫属。老家祖庙,三面环着岭坡,庙门前一湾清浅小溪欢快绕过,溪与庙间,围出一片鹅卵石铺砌的庭院,一樟一枫两棵百年古树参天蔽日,把天空遮个严丝合逢。树上浓密枝桠间,常年寄养着几窝喜鹊、几对松鼠,以树为家,人不扰它,它们也不怵人。暑天里,荫凉像水一样漫开,与日头底下截然两片天地。老人、孩子们拎着竹椅、夹着草席来树荫下乘凉,把席子铺开去,各户各家自成方圆,做作业、耍闹、打盹儿,逗松鼠、喜鹊玩,累了乏了仰面躺一会儿,感受丝丝凉风从发梢、腋下、鼻尖儿上幽幽拂过,苦暑不苦,伏天也不再难熬。
老人们说,老树与祖庙同龄,是盖庙时一同栽下的。这让我想到祖荫这词儿,也是我对祖荫最初的理解。
古人是深知树荫与水对暑日好处的。唐代高骈《山亭夏日》诗云:“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他告诉人们盖房同时要栽树、挖塘,有树有水才会招来荫凉的风来栖,这样的日子才好过。北宋词人秦观《桥南纳凉》也云“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塘自在香”。这是说晚上纳凉最好到池塘桥头南岸,柳枝依依,月明星稀,夜凉袭人,舒适极了。
暑日阴凉另一去处是竹林幽篁里。
竹子是世上最高茂的“草”,也是成林成荫效率最高的“木”,独树成林没有上百年也要数十年,栽下一竿竹,几年间就会衍生片幽篁浓荫出来。竹性清凉,竹叶青翠稠密,阳光经层叠竹叶筛滤,漏到地下只剩细碎的青莹光斑,光看这光斑就能生出丝丝凉意。风在密密青梗、稠稠碧梢间悠荡,如鱼得水,每一丝每一片都捎着滴滴水意,飒飒有声。乘凉找一片幽深竹林,确是个不错去处。
说起来,人们最初的房子就是用竹木作为框架,顶上披草木枝梢而成,其基本功能便是遮阴蔽雨,将生活与自然隔离开来。河姆渡先人们的杆栏式建筑,就诠释了这点。但是,仅有一片屋顶是不够的,隔离意味着封闭,门窗一关,风进不去,避暑乘凉还得另找地方。
我幼时,没事常往村后瓜棚跑,一畈瓜田中间搭一间竹凉棚,顶上覆以竹梢芦茅,四面透风,下面置一架高脚竹床,常见防蚊的纱帐在风中飞卷、漫舞。瓜棚的主人是我二伯。我去瓜棚的目的倒不仅仅为那口暴裂残次的脆生香甜,我更喜爱二伯的那架高脚竹床,往上面悠悠一摊,风从背脊下、肚皮上,脖颈、脚梗间肆无忌惮穿越、钻悠,舒爽惬意之极。
暑日另一阴凉去处是高墙弄堂间,墙越高、弄堂越窄,越阴凉宜人。峡谷效应让风在窄深的弄堂里左冲右突。高墙把烈日遮挡在外,风便自带凉爽湿意。铺一领凉席在屋弄里,四仰八叉摊下去,不要太惬意。
暑日阴凉,得找对地方。所谓“心静自然凉”者,真正是夹靴搔痒的风凉话。
寒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