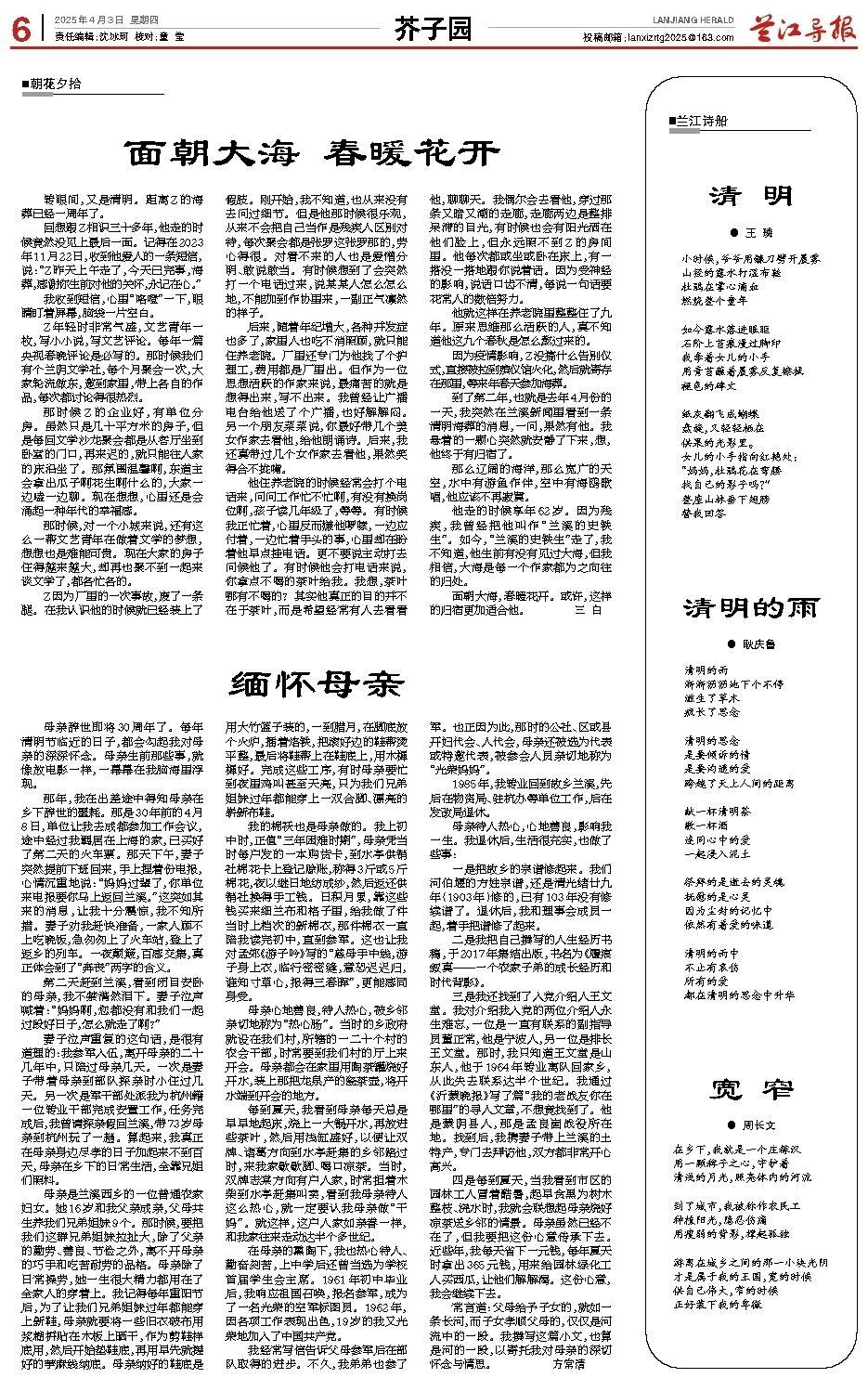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转眼间,又是清明。距离Z的海葬已经一周年了。
回想跟Z相识三十多年,他走的时候竟然没见上最后一面。记得在2023年11月22日,收到他爱人的一条短信,说:“Z昨天上午走了,今天已完事,海葬,感谢你生前对他的关怀,永记在心。”
我收到短信,心里“咯噔”一下,眼睛盯着屏幕,脑袋一片空白。
Z年轻时非常气盛,文艺青年一枚,写小小说,写文艺评论。每年一篇央视春晚评论是必写的。那时候我们有个兰阴文学社,每个月聚会一次,大家轮流做东,邀到家里,带上各自的作品,每次都讨论得很热烈。
那时候Z的企业好,有单位分房。虽然只是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是每回文学沙龙聚会都是从客厅坐到卧室的门口,再来迟的,就只能往人家的床沿坐了。那氛围温馨啊,东道主会拿出瓜子啊花生啊什么的,大家一边嗑一边聊。现在想想,心里还是会涌起一种年代的幸福感。
那时候,对一个小城来说,还有这么一帮文艺青年在做着文学的梦想,想想也是难能可贵。现在大家的房子住得越来越大,却再也聚不到一起来谈文学了,都各忙各的。
Z因为厂里的一次事故,废了一条腿。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装上了假肢。刚开始,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去问过细节。但是他那时候很乐观,从来不会把自己当作是残疾人区别对待,每次聚会都是张罗这张罗那的,劳心得很。对看不来的人也是爱憎分明、敢说敢当。有时候想到了会突然打一个电话过来,说某某人怎么怎么地,不能加到作协里来,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后来,随着年纪增大,各种并发症也多了,家里人也吃不消照顾,就只能住养老院。厂里还专门为他找了个护理工,费用都是厂里出。但作为一位思想活跃的作家来说,最痛苦的就是想得出来,写不出来。我曾经让广播电台给他送了个广播,也好解解闷。另一个朋友菜菜说,你最好带几个美女作家去看他,给他朗诵诗。后来,我还真带过几个女作家去看他,果然笑得合不拢嘴。
他住养老院的时候经常会打个电话来,问问工作忙不忙啊,有没有换岗位啊,孩子读几年级了,等等。有时候我正忙着,心里反而嫌他啰嗦,一边应付着,一边忙着手头的事,心里却在盼着他早点挂电话。更不要说主动打去问候他了。有时候他会打电话来说,你拿点不喝的茶叶给我。我想,茶叶哪有不喝的?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茶叶,而是希望经常有人去看看他,聊聊天。我偶尔会去看他,穿过那条又暗又潮的走廊,走廊两边是整排呆滞的目光,有时候也会有阳光洒在他们脸上,但永远照不到Z的房间里。他每次都或坐或卧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你说着话。因为受神经的影响,说话口齿不清,每说一句话要花常人的数倍努力。
他就这样在养老院里整整住了九年。原来思维那么活跃的人,真不知道他这九个春秋是怎么熬过来的。
因为疫情影响,Z没搞什么告别仪式,直接被拉到殡仪馆火化,然后就寄存在那里,等来年春天参加海葬。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去年4月份的一天,我突然在兰溪新闻里看到一条清明海葬的消息,一问,果然有他。我悬着的一颗心突然就安静了下来,想,他终于有归宿了。
那么辽阔的海洋,那么宽广的天空,水中有游鱼作伴,空中有海鸥歌唱,他应该不再寂寞。
他走的时候享年62岁。因为残疾,我曾经把他叫作“兰溪的史铁生”。如今,“兰溪的史铁生”走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有没有见过大海,但我相信,大海是每一个作家都为之向往的归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这样的归宿更加适合他。 三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