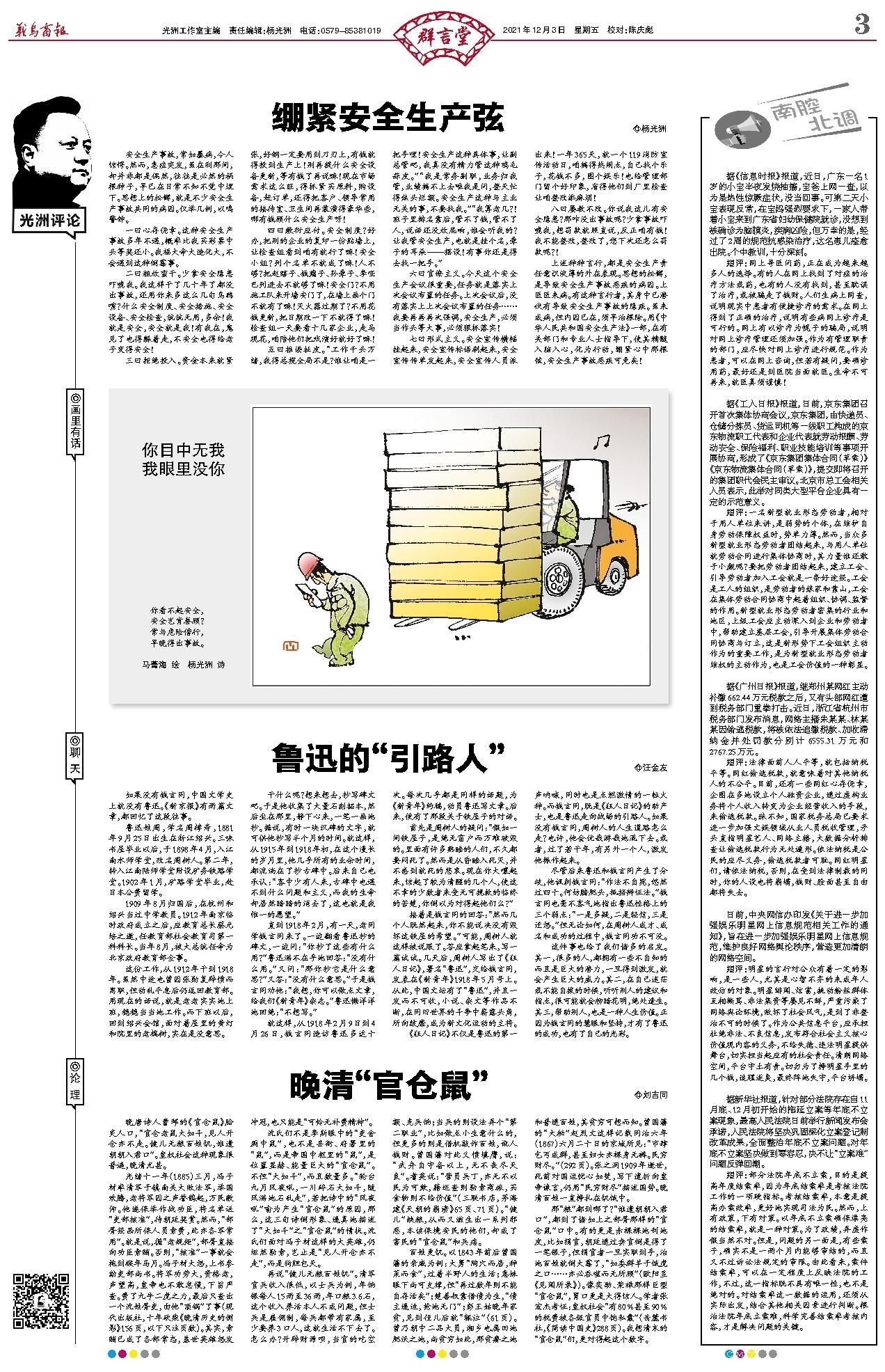晚唐诗人曹邺的《官仓鼠》脍炙人口,“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皇权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晚清尤甚。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冯子材率清军于镇南关大败法军,举国欢腾,老将军因之声誉鹊起,万民敬仰。他遂保举作战功臣,将名单送“吏部核准”,待朝廷奖赏。然而,“部胥径函所保人员索费,此亦各军常用”。就是说,循“老规矩”,部胥直接向功臣索贿。否则,“核准”一事就会拖到猴年马月。冯子材大怒,上书参劾吏部尚书。将军功劳大,资格老,声望高,皇帝也不敢怠慢,下旨严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只查出一个沈姓胥吏,由他“顶锅”了事(现代出版社,十年砍柴《晚清历史的侧影》156页,以下只注页数)。其实,索贿已成了各部常态,盖世英雄怒发冲冠,也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沈氏们不是李斯眼中的“吏舍厕中鼠”,也不是县衙、府署里的“鼠”,而是帝国中枢里的“鼠”,是位置显赫、能量巨大的“官仓鼠”。不但“大如斗”,而且数量多。“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若把诗中的“风夜吼”喻为产生“官仓鼠”的原因,那么,这三句诗倒形象、逼真地描述了“大如斗”之“官仓鼠”的情状。沈氏们面对冯子材这样的大英雄,仍坦然勒索,岂止是“见人开仓亦不走”,而是狗胆包天。
再说“健儿无粮百姓饥”。清军官兵收入很低,以士兵为例,年饷银每人15两至36两,年口粮3.6石,这个收入养活本人不成问题,但士兵是雇佣制,每兵都带有家属,至少要养3口人,这就生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开辟财源呗,当官的吃空额、克兵饷;当兵的则设法弄个“第二职业”,比如做点小生意什么的,但更多的则是借机敲诈百姓,讹人钱财。曾国藩对此义愤填膺,说:“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耆英说:“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三联书店,茅海建《天朝的崩溃》65页、71页)。“健儿”缺粮,从而又滋生出一系列邪恶,本该保境安民的他们,却成了害民的“官仓鼠”和兵痞。
百姓更饥。以1843年前后曾国藩的亲戚为例: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惠妹眼下尚可支撑,但“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楚善叔靠借债为生,“债主逼迫,抢地无门”;彭王姑晚年家贫,见到侄儿后就“辄泣”(61页)。曾乃朝中二品大员,湘乡也属田地肥沃之地,尚贫穷如此,那贫瘠之地和普通百姓,其贫穷可想而知。曾国藩的“大秘”赵烈文这样记载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的京城所见:“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292页)。张之洞1909年逝世,死前对国运忧心如焚,写下遗折向皇帝谏言,仍用“民穷财尽”描述国势。晚清百姓一直挣扎在饥饿中。
那“粮”都到哪了?“谁遣朝朝入君口”,都到了诸如上之部胥那样的“官仓鼠”口中。有的更是赤裸裸地刮地皮,比如捐官,朝廷通过卖官倒是得了一笔银子,但捐官者一旦实职到手,治地百姓就倒大霉了,“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亦必吞噬而无所顾”(欧阳昱《见闻所录》)。像奕劻、荣禄那样巨型“官仓鼠”,胃口更是大得惊人。学者张宏杰考证:皇权社会“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岳麓书社,《简读中国史》288页)。我想清末的“官仓鼠”们,更对得起这个数字。